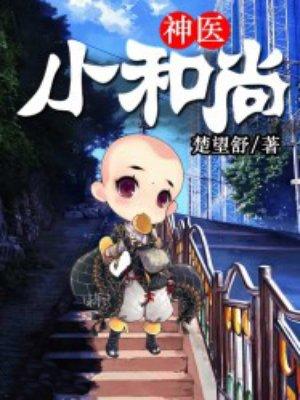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侯府主母重生和离 > 第38章 三十八章(第1页)
第38章 三十八章(第1页)
这厢,老太太听到远在洛州的沈三姨母来拜访,原本还带着笑意的脸,顿时沉了下去,极为不悦:“她怎来了?”
陈婆子也是愁:“这沈三姨母除了算起来也有好几年没来了,现在怎就来了呢。”
不知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莫不是想张罗着给侯爷纳妾吧?”
老太太捻着佛串,嘴角露出一抹讥诮:“还真是灶神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她一个外家的姨母倒是敢管到我这永宁侯府里头来。”
陈婆子不免担忧道:“那翁娘子现在有孕,若是被这沈三姨母气到了如何是好?”
老太太捻佛珠的手一顿,思索了半晌后,看向陈婆子:“她这么多年不怎敢来,我记得好像是因在老二媳妇那里吃了亏?”
陈婆子回想了一下,然后道:“好似是因撺掇着二房小娘多谋划些银子傍身,气得崔娘子连夜回了娘家,被大夫人赶走了。”
谢二叔院子里的唯一的妾室,还是沈三姨母婆家的庶女。
陈娘子想到这,说道:“这沈三姨母嫁到洛州后不过一年,有孕时婆母给她丈夫送了个颜色好的小娘,在她孩子生下后,与丈夫感情就淡了。”
“因她生的是女儿,而那小娘三年抱俩都是儿子,她对那小娘定是厌烦的,可又碍于是婆母送去的,她也不敢随意动,只憋了一肚子气。”
或许是因这个原因,她想到了自己的姐姐,所以到金都省亲的时候,带了个叔伯家软可欺的庶女过来。
原本是劝说姐姐收了的。理由是到时候老太太想要塞人进来,姐姐便以院子有人了来回绝老太太,也不会落得个善妒的名头。
夫人直接拒绝了,她又转而想去说服自己的姐夫。
可侯爷那性子说一不二,一句话直接回绝了,也不与她说二话。
沈三姨母一腔苦闷。
而那边二房的崔氏想看大房的热闹,就想着给她支招,不曾想最后支着支着,那洛州来的庶女竟与自己的丈夫看对眼了!
等发现的时候,已是珠胎暗结,为时已晚了。
自此崔氏与那沈三姨母也就不对付了起来
七八年前沈三姨母又来府上,去了世安苑去看那庶女。
瞧也就算了,还乱出主意让她为自己和儿女们多谋些银钱傍身,却不知那小娘身旁有崔氏的人,这些话都被崔氏听了去。
二人的矛盾便激发了,崔氏带着孩子便回了娘家,说是沈三姨母在一日,她便不回来。
自己的姊妹逼走了妯娌,这事传了出去,只会让自己脸上无光,更让自己娘家没了脸面。
侯夫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当即赶走了自己的妹妹,还让她没什么事别来侯府了。
那沈三姨母觉得自己一腔好意全被当成了驴肝肺,也就带着情绪离去了。
多年没来,直到奔丧那一年才来了一回。
老太太想起了这事,随即道:“那也就不用太担心了,不说老二媳妇防着她,就是我那孙媳的母亲也是个不简单的。”
连她都在那柳大娘子处吃了憋,更别说那拎不清的沈三姨母。
说到最后,鄙夷道:“她也不想想我永宁侯府的男儿那是要为国拼命的。如此,怎能被女色绊住了脚,又怎能因后宅的事情而在战场上分了心?”
才说着话,喜鹊便来通传,说是那沈三姨母来拜见老夫人。
老夫人面色沉沉,陈婆子瞧了一眼后,便会意的朝着门外的喜鹊吩咐道:“老夫人身有不适,不便见客,你让刘管事给三姨母安排一处离主院最远的住处。”
喜鹊应声退出了院子外,与那约莫三十来岁,眼尾皱纹明显的妇人说:“近来天寒,老夫人着了凉,身体有恙,所以不便见沈娘子。”
那妇人脸上的笑意略一僵,随后道:“那还真不巧了。”
婢女笑了笑,然后道:“老夫人吩咐了,让刘管事安排婢女收拾落英院给沈大娘子住下,好生招待。”
沈三姨母皮笑肉不笑的道:“那便替我谢过老夫人了。”
说罢就转身离去,离得远了,瞧了眼前边领路的管事,低声与身旁的婢女念道:“这老太太就是心眼多,我不过知礼数,好心来看望她,她倒好,早不病晚不病,现在却装病给我拒在了门外!”
婢女小声附和:“老太太心偏着二房呢,大姑娘和大姑爷这都不在了,她便瞧不起沈家人了。”
沈三姨母脸色沉了沉:“若瞧得起,怎会同意了玦哥儿把那样身份的女子带进了侯府?”
“就算是带入了府中,给个贵妾的身份便也就罢了,为何还要让那女子做了正妻,这不是明摆着对这个孙子不上心么。”
身旁的婢女顺着主子的话说道:“姨母到府中,也不见那翁氏来迎接,这便罢了,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可见那翁氏的礼数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