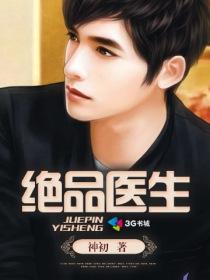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哭泣的骆驼歌曲廖昌永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ldo;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rdo;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糙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ldo;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rdo;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ldo;荷西,你看这个,&rdo;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ldo;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rdo;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ldo;三毛,你看他的脚趾。&rdo;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ldo;麻疯吗?&rdo;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ldo;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rdo;&ldo;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rdo;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ldo;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rdo;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ldo;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rdo;我叹了口气。&ldo;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rdo;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ldo;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rdo;
&ldo;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rdo;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ldo;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rdo;
&ldo;谢谢!&rdo;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ldo;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rdo;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ldo;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rdo;荷西苦恼的说。
&ldo;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rdo;
&ldo;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rdo;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ldo;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rdo;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ldo;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rdo;
&ldo;永远不会,永远。&rdo;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ldo;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rdo;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ldo;谢谢、谢谢!&rdo;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ldo;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rdo;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ldo;我们能签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