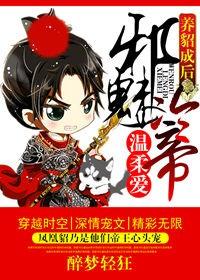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黑色记忆棉和白色记忆棉枕头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惊讶的喊声:&ldo;谁,谁在湖里?!&rdo;一道手电筒的光线打过来,紫灵望着湖边,几乎虚脱地招手,&ldo;曹沉老师,是我,紫灵。&rdo;
湖边有人回应了,薛白杨再回头看身后,黑影连同影子里面的那张脸一起消失了。
十分钟后,两个人疲惫地瘫坐在湖边。身形矮小,面色焦黄的s师范大学的曹沉老师上下瞅着两个人,最后目光定在了薛白杨脸上,猛地拍了拍薛白杨肩膀,&ldo;我想起你来了,昨夜在这湖边昏倒的那个男生就是你,没错吧?还是我把你给送回学校里的。&rdo;
薛白杨脸色苍白,尴尬地笑了两声,不知怎么回答。
曹沉老师摇摇头,又望了望旁边的紫灵,稍微小声说:&ldo;上次他们说你是为情自杀投湖,我还不相信。现在信了。&rdo;
薛白杨连忙摆手,想澄清。曹沉老师却将目光转向了紫灵,语重心长地说:&ldo;紫灵啊,恋爱这个东西曹沉老师也经历过,理解喜欢一个人不容易,但你看这个小伙子这么喜欢你,为了你自杀两次了,就给他个机会吧。&rdo;
紫灵目光闪啊闪啊,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微微点头。
薛白杨干脆不说话了,现在,他已经到了百口莫辩的地步。
无论如何,这次他跟紫灵又一次经历了生死冒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像更进了一步。而紫灵也萌发了她新的小说的创作灵感,唯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用相机记录下那惊心动魄的时刻。
就当薛白杨以为自己同紫灵的感情会突飞猛进的时候,紫灵这妮子却再一次消失了,依然是电话关机,打了几十次也没人接。薛白杨想去找她,但贸然去找个女孩,鲁莽了些。鬼湖历险之后的一个星期,薛白杨一直没有紫灵的音讯。
周一参加完社团活动后,薛白杨很晚才回到寝室。寝室里的人都睡了,老牛给他留了一盏台灯,薛白杨端着盆子来到洗漱间洗漱,嘴里塞着牙刷。薛白杨没来由的突然一阵心颤,感觉跟第一次在鬼湖撞鬼时的心悸差不多。薛白杨出神地看着昏暗灯光下的洗漱镜,微微摇头。待薛白杨收拾妥当转身走向寝室,身后突然传来了古怪的声响。
咔咔咔‐‐像是骨骼在爆裂的声音,薛白杨扭头大声喊:&ldo;谁,谁在那里?&rdo;
跟预想一样,没有人回应薛白杨。薛白杨侧着身子,探了过去,目光投向洗漱间的瞬间,一个黑长的影子映进了他的眼睛里。薛白杨被吓了一跳,踉跄着险些跌倒,待站稳了才看清不知是哪个浑蛋竟把拖把搭靠在了窗口,乍一看,就像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窗边一样。薛白杨心中将这个放拖把的人骂了几十遍,然后来到窗口,将拖把随手扔回到角落里。
微侧目,对面的女生洗漱间里也亮着一盏白灯,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孩正背对着窗户,站在窗边,抚摸着乌黑的长发。
老天,从天而降的眼福!嘿,可惜老牛这爱激动的厮没看见。薛白杨将脸贴在窗户上,目光眨也不眨地望着对面,对面女生洗漱间里的女孩穿着一件粉红的小背心,衬得她的肤色很白,用那句话来说,就像是牛奶混合蜂蜜的肌肤。薛白杨心里痒痒的,虽然他并无恶意,但像他如此年纪血气方刚的男生,又有几个能够忍住不偷偷张望几眼的。
女孩一直侧摸着头发,薛白杨惬意地欣赏她后背优美的曲线。但不久,薛白杨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这女孩摸了好一会儿的头发了,怎么还在摸?他睁大了眼睛,想瞄瞄女孩的脸,但女孩的脸被黑发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
女孩终于停止了抚摸头发,黑色长发像瀑布披在她背脊上,而女孩也缓缓地转过头来。薛白杨有些激动了,终于要看见这拥有绝美背影的女孩的庐山真面目了,心头一阵小激荡。
女孩一边转头,一边更靠近窗边,头完全转过来的刹那……
灯‐‐熄灭了。
女生洗漱间灯光消失的同时,薛白杨所在的洗漱间也陷入黑暗里,薛白杨眼前一片漆黑。靠,偏偏关键时刻停电!薛白杨埋怨着。一阵小风从窗户缝里吹了进来,薛白杨觉得脖子后突如其来的一阵麻痒,有点像是头发在脖子后面轻轻地划拉,历经种种诡异的薛白杨脑海里浮现出许多不好的预感。他伸出手,摸向自己脖后。
脖子后面,薛白杨的手摸到了另外一只手,冰冷如石,一点温度也没有!这冰凉顺着手传遍了薛白杨全身,吧嗒一声,灯光重新亮了。
耳边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ldo;你抓住我的手做啥,搞gay啊?好心帮你拿掉你脖子上的一只蚂蚁,真是的。放开,肚子疼死了!&rdo;是老牛的声音,薛白杨转头,果真是老牛。这家伙不知啥时候跑到自己屁股后面。他松开手,老牛忙不迭溜进了厕所隔间里。
对面的女孩呢?薛白杨想起来,再看时却发现,对面女生洗漱间里仍旧是一片黑暗。
她应该是回去了。薛白杨这样想,兴味索然地走进了寝室。
这一夜,薛白杨辗转反侧,总也睡不着。迷迷糊糊间,他似乎看到了一张脸,一张藏在黑黑长发中的脸,紫红色的伤疤、漆黑无眼白的眼球、白森森的牙齿,是那张鬼脸!
&ldo;呼!&rdo;薛白杨从床上坐了起来,天已经亮了。
薛白杨懒洋洋地坐在餐厅一角,寝室里的另外两个家伙‐‐老牛跟方中交头接耳地坐在一处,评论着前面一桌女生的样貌。薛白杨眼皮发沉,昨夜接连的梦境让他无法睡得安稳,想此时眯一会儿,可前面桌的女生唧唧喳喳的说话声跟蚊子一样钻进了他的耳朵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