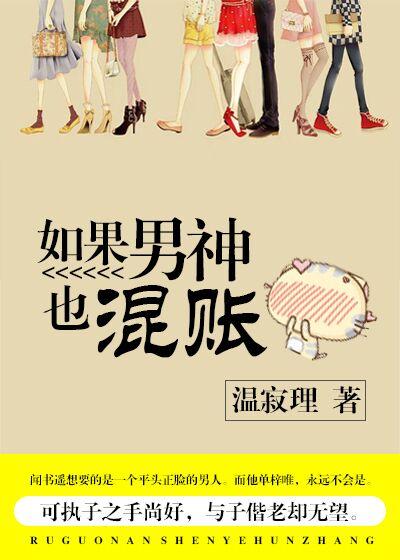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恋曲1999罗大佑歌词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胡达背着吴久生走了一段,他怕青年无聊,便想着法子找些话题,和他说自己小时候的事。说村里养的几只大黑狗,其中一只是狗王,走在路上一眼就能认出来,和方圆十里的狗打架都打了个遍,还从来没有输过。也说起男孩子调皮,听家里的老人回忆当年忍饥挨饿的年代连玉米棒子里的芯子都吃得精光,就自己偷拿玉米棒把外面一层好好的粮食剥掉,芯子扔进大磨子里,磨出来粉下锅里炒,再放进嘴里干嚼,嚼得辣嗓子四处找水喝。还有到小水塘里比赛憋气,赤脚蹲在河岸的浅滩上搬石头,抓石头缝里的小螃蟹,钓小龙虾,找螺丝
胡达生长在米面粮油都还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他这辈子,连婴儿奶粉都没吃过,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专给孩子玩乐用的好东西,他的童年过得十分野生,一张画片,路边的几粒石子都能当做是新奇的稀罕玩意,长到十几岁才看到第一本漫画,才知道鸟山明和七龙珠,可那时他已经过去了会对那些东西感兴趣的年纪,成了个不再愿意简简单单做梦,满脑子只有挣大钱出人头地的叛逆青年。
这世上了解他的人只有祖母,她大概早已经看出胡达身上的躁动和不安分,早在胡达成年离开家乡南下之前,就把胡达叫到身边,塞给他一副自己当年陪嫁用的金镯子和一副银耳环。
那两样东西来自战争年代,是她一生珍藏的爱物,耳环是逃难期间用家里仅剩的一块袁大头融了找银匠打出来的,挺过了一路的山长水远和艰难困苦,现在传给孙子,原是想叫他拿来,送给日后的心上人,当做聘礼,为胡家娶孙媳妇用的。
也许一个安分贤惠的女人能稳住一个毛头小子身上的冲动,让他的一颗心定下来,找到归处,找到家。
可惜老人的用心良苦,年轻气盛的少年人并不能懂得。胡达拿苦笑掩饰着眼神中的懊悔,告诉吴久生说自己当时是多么不懂事,到了深圳以后日子过得吃紧,在自己白手起家做小生意之前为了手头能有一点现钱,随便找了家铺子,把镯子和耳环当掉了。
后来他入狱又出狱,开起了小饭馆,生活稳当下来以后,曾经短暂地想过要不要托找关系,寻到当年的当铺老板,看看还有没有一丝希望能找回祖母留下的遗物。可每当他准备尝试那样去做的时候,内心里又犹豫了。
他明白祖母的心愿。对于老人来说,重要的恐怕并不是一件两件的饰物,而是那个她作为长辈心心念念像要的孙媳妇。那是胡家的后代,是胡家的根,理应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绵延不息。
但胡达没有做到,即便寻回那几样死物,他也是清楚的,自己让祖母失望了。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不要去找回来。不要去想,不要去见,十几年不回老家,仿佛只要一直逃避在外,这样艰涩的难堪就可以不用去面对。
可现在不行,他终究还是回来了。
蹲在山阴面的坟头前,胡达烧完了整整一沓的纸钱。他有些哽咽,强压住了,抓住一旁立着的吴久生的手,对着面前的石碑说:
“奶奶,这是小久,我带他回来看看,你看看,他挺好,真的,一点也不差。”
就是做不成媳妇,给不了你孩子,没法给胡家留下后代延续血脉,吴久生闷闷地想,他把胡达没有说出口的话已经全在心里默默说完了。
“对不起”他也对着那块石碑,心头歉疚地深深鞠了一躬。
那夜,两个人都没睡着。
上下山又花去大半个白日,接连两天没有休息,都乏得厉害,受冻又没有吃好,腿脚又酸又软,守着黑洞洞又半点热气没有的屋子,只觉得眼眶都生涩着疼。小地方小村落过年并没有多少讲究,没有扰民这一说,家家户户都放鞭,入了夜以后放得更是卖力,一声连一声炸个不停,仿佛就要那样一直炸到天明,炸到日历翻到新的一年那时候去。
窗玻璃像在震动,床板像在震动,天地都无一处安详,山摇地动的,根本也没法睡觉。
吴久生裹着大棉衣一骨碌从床里爬起来,打墙边随手抓了一根枝条就推开门往灶房那边走。除去住人的主屋,撇开柴房和灶房,院子里还有两间小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吴久生大半夜的,想推门过去转转。
胡达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夜里探秘的欲望,追着青年下地,想把人重新捞回来。
“柴上午我砍过了,炉子里有火,壶里有水,没有需要你干的活,你去院子里做什么?”
“熟悉熟悉环境。”吴久生头也不回地说,“你家这种烧柴的炉灶我还不会用呢,我得学学怎么使它,至少得能用它学着做点饭出来吧。”
“做饭有我,你担心什么。”胡达好笑,想不通青年身上突然发起的这股勤快和执着是怎么回事。
吴久生却不以为意。
“迟早是会用上的。”他回答,“我给你生不了孩子,你没孩子,到老了就只能我来给你操持,到时候你要是老得都走不动了,想叶落归根回到故里,我总得学学怎么在这间屋里生活吧。我得给你做饭,给你烧火,得给你洗衣服,还得找人上山给你看风水,选块宝地,不叫你以后像那样阴寒着受冻,也不用我每次去看你,都走这么远的一程路,路上耗的时间太长,我就不能时常过去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