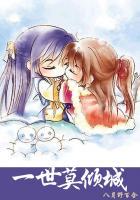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厄兆方舟 > 第83章(第1页)
第83章(第1页)
但她不敢等到它变为&ldo;成见&rdo;。
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
泰德没有注意到,那条狗也没有注意到。肯定是这样,所有的推理都断言是这样。那声沉闷的声音,她拉门时发出的另一声沉闷的声音,门关上时砰地再一声重响。如果它在车前,这些声音会让它发作起来。它大概在谷仓里,但她相信它在那儿也能听见这里的嘈杂声。它一定是游荡到什么地方去了。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即使她吓得不敢为自己冲出去,她也决不应该吓得不敢为泰德冲出去。
真是高尚得恰到好处。
但最终说服她的,是一幅她进了坎帕家后的幻景,和那种手头有电话的让她放心的感觉。她能听见自己在和班那曼长官的一个助手交谈,相当镇静。理智,然后把电话放下。然后去厨房找一杯凉水。
她又把门打开,这次她已经对那种沉闷的声音做好了准备,但它真的发出来的时候她还是缩了一下。她在心里诅咒着那条狗,希望它已经躺倒在某处,死了,身上爬满了苍蝇。
她把腿转出去,它们僵硬。发疼,这让她缩了一下。她的网球鞋踩上了地面。她逐渐在黑暗的天空下站了起来。
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只鸟在叫,它叫了三声,停下了。
库乔一直昏迷不醒地卧在汽车的前面,后来它在几声重响中醒了过来。它听见门开了,直觉告诉它它会开的。
它几乎就要绕过去抓住那个女人,她让它的头和身体可怕地疼痛着。它几乎就要绕过去了,但直觉命令它们静静地卧在那儿,那个女人只是试图引它出来,后来这被证明是对的。
当疾病在它身上缩紧,渗透进它的神经系统,就像草原上贪婪的野火,在四处升起鸽灰色的烟,燃起玫瑰色的火焰,接着又开始摧毁它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时候,它也加深了它的狡诈。它一定要抓住那个女人和那个男孩,他们造成了它的痛苦‐‐它身体里的痛苦和它脑袋里的刺痛,那是它一遍一遍撞向那辆汽车时产生的。
库乔今天有两次忘了那个女人和那个男孩,它离开谷仓里的那个狗避难所‐‐一乔&iddot;坎泊在后屋;&rso;河上挖出来放帐单的一个大洞‐‐下山去了后面的沼泽,两次立都很近地经过了那个住着编福的石灰石洞穴的大开口。
沼泽里有水,它也非常渴,但每次真的看到那些水时,它又都会狂暴起来。它想要喝那水,杀了那水,在那里洗澡,在里面拉屎撒尿,让它盖满脏物,摧毁了它,让它流血。每次这种狂乱的想法都最终又让它离开,它会鸡鸣叫着,浑身颤抖。这都是那个女人和那个男孩造成的,它不会再离开他们了。
没有哪个生活过的人会发现有一只狗这样忠于信念,这样执著于它的计划。它会等,直到它抓住他们。如果需要,它会等到世界的未回。它会等,它会守望。
主要是那个女人。她看着它的样子,好像在说,是的,是的,是我做的。我让你生病,我让你刺痛,我专门为你设计了痛苦,从今天起这痛苦会永远跟着你。
噢,杀了她!
杀了她!
一个声音出现了。
那是一种轻轻的声音,但它没有逃过库乔的耳朵;它的耳朵现在已经能超自然地调向谷种声音了,声音世界里最完整的谱就是库乔的音谱了。它能听见天堂里的钟声,它能听见从地狱里传上来的嘶哑的尖叫声,疯狂之中它可以听见真实和不真实的声音。
那是一种小石头间相互滑动、相互摩擦的轻音。
库乔的后腿在身后紧紧地压着地面,只等她出来。尿,热而痛苦,毫无顾忌地流出来。它在等那个女人出现。她出来的时候,它会杀了她。
特伦顿家楼下的废墟中,电话铃开始响起来。
它嘶哑地叫了六声,八亩,十声,然后沉默了。紧接着,特伦顿家订的罗克堡《呼唤》报砰地撞到门上,比利&iddot;弗里曼肩头背着帆布包,吹着口哨,踩着车继续向瑞利家骑去。
泰德屋里的衣橱门开着,一种说不出的干热的气味,凶暴而野蛮,迷漫在空气中。
在波士顿,一个接线员问维克&iddot;特伦顿要不要她继续试试,&ldo;不,这就行了,接线员。&rdo;他说着挂断了电话。
罗格在38频道发现了红星队和堪萨斯城队的比赛,他穿着内衣坐在沙发里,面前放着由服务员送进屋的一块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正在着队员们做热身运动。
&ldo;你的那些习惯中。&rdo;维克说,&ldo;大多数都具有主动的冒犯性,至少也让人厌恶,我觉得其中最糟的大概就是穿着内裤吃东西了。&rdo;
&ldo;听听这个家伙的话。&rdo;罗格对着面前的空气温和地说,&ldo;他三十二岁了,还把内衣短裤称之为内裤。&rdo;
&ldo;有什么不对吗?&rdo;
&ldo;没什么……除非你还只是个夏令营里不开化的小孩。&rdo;
&ldo;我今天晚上会割断你的喉咙,罗格。&rdo;维克快意地说,&ldo;你会醒来,发现你倒在自己的血泊中,你窒息了,你会想道歉,但……太迟了!&rdo;他拿起半决罗格的熏牛肉三明治,狠狠咬了一口。
&ldo;真他妈太不正常,&rdo;罗格说,他把三明治的屑子从裸露的毛绒绒的胸前掸掉,&ldo;多娜不在家,嗯?&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