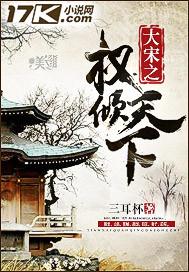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江山别夜苏眠说那女主角 > 第20章 星贯紫微(第2页)
第20章 星贯紫微(第2页)
薄安迈正步走到殿前,将儒冠先除去,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地上。殿中一时没了声息,但见他双膝跪地,三叩首道:
“臣等有罪,令陛下生外家跋扈之疑,今臣自请免官还第,请陛下成全!”
仲恒的目光投注在他身上,带着三分端详和七分冷淡。
薄安又叩首下去:“请陛下成全!”
皇帝突然站起身来,拂袖道:“退朝!”
皇帝弃了车,径从殿上复道往昭阳殿行去。复道上的直棱窗糊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冷风,然而皇帝的袍袖依然带起了猎猎风声。冯吉在皇帝之后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冷不防皇帝一停步,沉声发问:“梁王今日怎么不来上朝?”
冯吉眼帘微垂,“回陛下,梁王殿下今晨派人来告了假,道是昨日游冶无度,伤了一只手,无法面圣。”
皇帝眉头一动,“伤了一只手?严重么?”
冯吉态度平静,好像他根本没有感知到皇帝话语里的关怀一般,公事公办地回答:“殿下不肯就医,似乎并不严重。”
皇帝点了点头。昭阳殿眼尖的女官已望见了圣驾,立刻准备了起来,过不多时,梅婕妤便在殿前严妆迎候。皇帝踱步而前将梅婕妤扶起,拍着她的手寒暄几句,忽然又转头问冯吉:“十月旦的宫宴上,太后似乎跟朕提起了一个人?”
冯吉压弯了腰,无人能看见他的表情:“是,广元侯流落在外的女公子前些日子已认祖归宗了。”
“朕听闻这薄家女郎还曾是梁王宫里的侍婢?”
冯吉顿了顿。
“是。”
“让她过来见朕。”皇帝说着,拉着梅婕妤的手往昭阳殿中去了。梅婕妤低声与他盈盈笑语,他的脸上终于绽开了夙日不见的笑容。
“——什么?!”
“哗啦”一声,案上简册都被拂去,顾渊“唰”地站了起来,身形笔直如剑,眉目中尽是凛冽剑气:“再说一遍。”
孙小言战战兢兢地道:“陛下、陛下宣阿暖去昭阳殿面圣,现在女郎大概已在路上了……”
顾渊一步迈过了书案,双袖平举抖了抖,“给孤更衣!”
孙小言吓了一跳:“殿下这是要去哪儿?”
“给孤更衣。”顾渊冷冷地道。
孙小言只得去衣桁上取下他的常服,想了想,又放回,拿了一套朝服来,顾渊扫了一眼,轻轻哼了口气,没有指责,那便是默许了。
孙小言给他扣上玉带钩,他自己又下意识地紧了紧。孙小言咽了口唾沫,终究没能忍住劝谏:“殿下这会儿去面圣,那才前想好的手伤不朝又怎么解释?今日朝议闹得凶,陛下召见阿暖,或许只是为了让广元侯宽心罢了……”
“你知道孤最恨陛下什么吗?”顾渊突然转过身来,直直注视着他。
这话大逆不道,但大逆不道的话顾渊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孙小言有些不敢听,低了头哈了腰不知怎么接的好,顾渊已冷冷续道:
“孤最恨他用女人作饵。十三年前,十三年后,一模一样。”
孙小言呆住。
梁王已径自离去了。孙小言看着那挽起的晃动不已的梁帷,心中慢慢盘算着:十三年前……十三年前,是玉宁八年。
玉宁八年,陆氏谋反族诛,陆皇后忧死。
昭阳殿前殿。
薄暖已跪了两个时辰。
盯着那一扇十九折的琉璃镶青玉屏风,她脑海中响起了另一个人淡静的声音:“当孝愍太子在的时候,孤每到宫中赴年宴,第二日清晨往温室殿去请安,都要跪上三五个时辰……孤的母亲与孤一同跪,就跪在前殿的屏风前……等陛下跟里头的夫人出来,那屏风都快被孤盯出洞来了。”
她拧动发酸的脖颈望向殿边铜漏,却原来只过了两个时辰。不知那人每年是怎样熬过这三五个时辰的?这可不同于跪在外面。殿间那珠粉色的纱幔微微拂动,旖旎而引人遐想,令她感到窘迫——
皇帝为什么要在这里宣召她?
最最不可理解的是,皇帝为什么要宣召她?
忽然有女官自内殿走去,急急提醒了句:“陛下来了。”便去殿侧掌起灯火。一时灯烛高烧,将这暮色沉沉的前殿照得一片通明,而皇帝在冯吉与几名内侍的随同下缓步走来了,并不见梅婕妤的影子。
皇帝绕过那屏风,走到殿中央的蒲席前,屏退了左右,才淡淡地道:“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