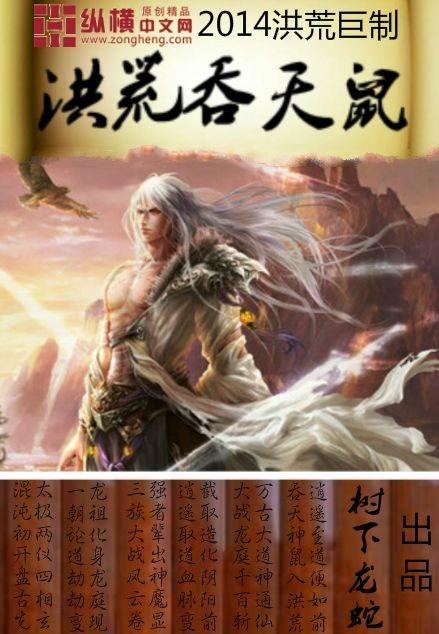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连哭都是我的错粤语版叫什么 > 第195章(第1页)
第195章(第1页)
她想要我后悔,想要我死,我照做就是。
从小到大,妹妹们要的,我什么没给过?
嘴角浮起一丝凄凉而释怀的笑容,泪水打湿了我被割破的皮肤,也打湿曾经纯白的记忆。
只有失去拿命捍卫的一切,我才清楚,这世界纵使再华丽,不过是座玩具盒子般的空城。
我在这座城,背着无数错误,孤勇前行,如同背着无数巨大的伤口。
世界不断更新,伤口也跟着不断更新。
世界越更新越肤浅,伤口越更新越深刻。
最后,世界肤浅得露骨,伤口深刻得刺骨。
我和幼清的存在,本身便是不可言说的伤。
只是当时,我们无从得知真相。
我们的母亲,叫花阳,是个不温不火的作家。
我们的父亲,叫水耀灵,是个名震业界的心理医生。
不过,五岁以前,父亲对我们来说,只是照片里的一张脸。教我们说话、走路、读书、写字,陪母亲对抗的抑郁症季叔叔,充当着父亲的角色。
年幼的我们曾经觉得,继续站在季叔叔那边坚持下去,我们能赢。
母亲不会再因为没看到父亲的尸首,而一意孤行地守着照片死等。
可……我们输了。
尹鸩夫妇的突然到来,害季叔叔在我家餐厅里,被一个陌生女人,用牛排刀刺破颈动脉,当场死亡,在我们的生命里,刻下了第二道不可愈合的伤。
但六岁那年,父亲突如其来的出现,让我们一家重回平静的生活,母亲的抑郁症渐渐好转,小妹妹很快诞生,我也便放下了恨。
父亲给小妹妹取名叫若烟,浮梦若烟的若烟。
在若烟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就总是喜欢在婴儿床边不断声声地叫她的名字。
我会在爸爸照顾妈妈忙不开的日子里,抱着若烟给她讲《安徒生童话》,拿尤克里里给她弹《致爱丽丝》,教她用不同的语言叫&ldo;妈妈&rdo;、&ldo;爸爸&rdo;、&ldo;哥哥&rdo;、&ldo;姐姐&rdo;……
五年后,尹鸩夫妇再次到来,于我而言,仅是平添几分拉着幼清欺负简亦凡、调戏尹蜜,然后讲给若烟听的恶趣味而已。
我从来不曾想过,又过了一年,尹鸩夫妇竟会害我癌症晚期的母亲丧命,害我深受打击的父亲患上尿毒症。
许是愧疚使然,简瞳没有让我们一家回到法国,而是把我们养在凇城,给我父亲治病,资助我们兄妹念书。
我逐渐淡忘了当初在机场发的誓,认为尹鸩夫妇或许真的只是想帮我们的母亲达成年少时去挪威看极光的渺小梦想。
结果,高二那年,简瞳夫妇来看望我父亲,发生了口角。
我在门外听到简瞳说,当年我父亲有幸错过空难,却被尹鸩为了纪心爱逼迫出国。
母亲抑郁症的罪魁祸首……是尹鸩!
他们夫妇特地把我们的住处安排得很远,特地避免我们兄妹和他们儿女的接触,无疑是怕遭到报复!
父亲听到他们的争吵,第一次知道害他和母亲分别五年的始作俑者是谁,怒火急火齐齐攻心,病情恶化,抢救失败。
我们的生命里,被刻下第三道血淋淋的伤口。
换谁谁能不恨呢?
无奈当时的我和幼清还要照顾年幼的若烟,没能力也没精力筹谋报复,于是听从简瞳的安排,回到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