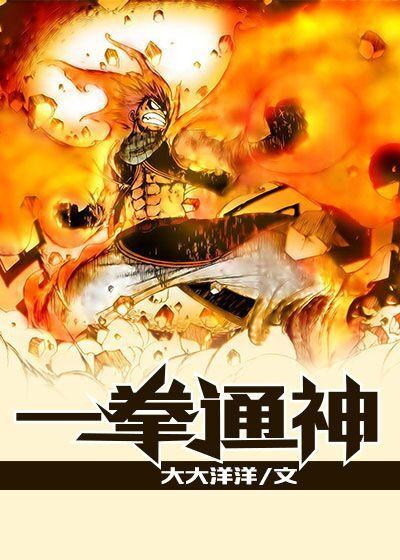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将军媚无尘大结局 > 第68页(第1页)
第68页(第1页)
他嘻嘻一笑,意兴疏狂:“怎么,本王可有说错?”只略改了后面一句话,便将太子气得怒气勃发,他暗讽太子不过是借着祖荫,来享太子之位,实则没有半分功劳,就如那些犯了罪,但借着家里有钱有势,依旧可以逍遥法外的人一样。那些官员虽然站起了身,可太子没有发话,却是只能气呼呼地又坐了下去。我瞧见太子脸色虽极为平静,但拳头却是捏得极紧,过了好一会儿,才将那拳头缓缓地松开了。我在心底轻轻一笑:你虽养气功夫极佳,但这,才是乌木齐,真想再气人乌木齐既是只找太子的麻烦,夏候商和夏候昌自是不便开口,但我站在夏候商的后面,却瞧见他的耳朵上青筋都冒出来了,说得也是,当年他带兵与西夷军交战之时,亲上战场杀敌,直杀得后面西夷军闻夏候商之名而闻风丧胆,哪轮得到乌木齐在此大放厥词?可人家不是找的他,讨论的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他如何能插言?所以,他只能静静地坐着!再说了,他昨天才得了一项好处,今天见了太子,脸色就有些不自然,虽说人家太子脸色从容,仿佛不以为意,行礼之时依旧是弟恭兄亲,但他却是怎么还敢出头给太子添堵?所以,我认为,夏候商坐着的虽是黄杨林铺了锦缎的椅子,恐怕也如坐在热锅上差不了多少。还好,殿内安静了不一会儿,皇后皇上便驾到了,又隔了一会儿,皇太后拄着龙头拐杖也满脸慈祥地出现了。三位至尊贵人在堂上坐定,乌木齐倒是神情恭敬起来,酒也不喝了,端端正正地坐着。那身姿仪态比礼部侍郎更为标准,有心人见了更是忿忿不平,他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旁人,他只尊皇帝皇后,皇太后,所谓太子,只配让他草莽相交吗?又是一翻忙乱行礼,各部官员和皇室子弟坐定,乌木齐也跟着坐定。皇太后目光如注,哪壶不开提起了哪壶:“噢,乌木齐王子,您没来天朝几日,礼仪倒是学得中规中矩,可难为你了。”我不相信刚刚发生的事,就没个人传进皇太后的耳内,看来老佛爷是故意如此的。乌木齐对太子不恭倒没有什么,但皇太后的揄揶,却让太子脸色一白,眼底又是一红。这老太太记仇呢,寿景宫发生的事还没完!太子想要重获老太太的欢心,看来得有些日子了。皇帝到底是偏坦自己这个儿子,咳了一声道:“母后,时辰既到,开席吧。”皇太后恩了一声。手持拂尘的太监一声唱诺,宫人们端了红漆木盘将菜流水一般地送了上来,绡纱扫过无尘的地板,乐师奏起了中韵和乐,悠扬平和的乐音与满室的菜肴香味,略略减少了一些厅内的紧张气氛。皇太后起筷之后,皇帝皇后便笑着恭请群臣,还特地赐了几样颇具草原特色的菜肴给乌木齐。开席之后,歌舞跟着上来,皇家歌舞,自是宏正大气的,虽是舞姿奥妙,舞技如仙,可每一次宴请,差不多都是这些,所以,厅内之人看的没有几个。乌木齐更是显得兴味索然,抬头不过看了几秒钟,就开始吃桌上的菜了。原本这宴请也不过是为了彰显大国气势,依照旧例而行,可乌木齐那厌厌之色表现得太过明显:两个歌舞之后,他微闭着眼睛坐在椅子如和尚一般地开始入定了。这下皇帝看不下去了,坐于上首的皇太后脸上都没有疲色,你倒先疲倦了?所以,他一挥手,让歌舞退下,向乌木齐道:“乌木齐王子,这菜可合您的胃口?”乌木齐浑身一颤,睁开了眼,很像是在睡梦中被人打扰了的样子,慌慌的向皇帝拱手道:“皇上,对不住,本王是个粗人,听惯了草原上粗邝的嘹歌,您这些柔软亲媚的歌舞一起,本王便如躺在篓中,忍不住想睡了。“皇帝脸色都变了,他辉鸿大气的皇家歌舞比喻成摇篮曲!虽则乌木齐这次是来上贡求和,以示百年之好,但他一再的挑衅,却让堂下人人都怒气难平,心想不过一个战败之国而已,尚且如此嚣张!可人家又说了:“皇上,臣下说话直爽,但大漠草原上的人大都如此,你可别怪责臣下,哎,怪只怪臣下见识短浅,听不惯这文质彬彬的音乐。“你能责怪他吗?人家已经认错了,还自承其短,责怪他,就显得天朝臣子没有气度,没有风度。所以,皇太后最后当了和事老:“那依乌木齐王子的意思,这夜宴,要些什么节目才能让你不打旽呢?“人人都听清了皇太后语气中的讥讽之意,偏乌木齐这时却听不出了,他兴致勃勃地介绍:“每到年假节日,我们草原上的族人便会聚集一起,赛马,相扑,射箭,跳健舞,赢者,赢了的,才可得到草原上最美姑娘的青睐。有别国使者前来,便请他加入我们的草原大会,以大碗斟酒,用银刀割烤好的羊肉相请,如有擅武,更是邀请其进行相扑……”皇太后听得不耐烦了,淡淡地道:“那倒是对不住了,此乃天朝,自有天朝风俗,王子如果似那幼儿,耐不得久坐,要不要哀家准备个睡榻换了你那张椅子?”此话一出,堂内众人皆哈哈大笑。那三皇子夏候昌年青气盛,早憋了一口气,更是叫出了声:“皇祖母,说得好!”乌木齐当既离座,口称该死,道:“皇太后,臣下该死,喝多了几杯酒,口出狂言,原是想西夷天朝既已交睦邻友好之邦,臣下便如您的孙儿子侄一般,因而未免放肆起来……”皇太后截住了他的话:“所以哀家才让人给你准备张榻啊!”此话一出,堂下众人又是一阵大笑。乌木齐以四肢伏地,行了一个大礼,等笑声止歇,才道:“皇太后,臣下没有旁的意思,只是想着西夷天朝原来交战连年,双方百姓死伤不少,既已和谈,便应放下一切恩仇,双方罢兵止刄,因而臣下此次前来将引得贵国军队如溃堤之势的罪魁祸首:勾刺箭也带了过来,以表我族永远罢用勾刺箭,以定与贵国休百年之好的决心,从此以后,勾刺箭便不再用于战场,只供玩乐舞宴,所以,臣下肯请,可否让臣下以勾刺箭为戏,博皇太后一笑?”此番长篇大论一出,连平日里泰山崩于眼前都不动声色地皇太后当既站起身来,神色更是大怒,众人皆听得明白乌木齐看似恭敬实则张狂无比的一翻言论:我族仅用一供以玩乐的勾刺箭,就让贵国军队损失过万,如溃堤之势地败走,贵国放心,我国既与你国交好,绝不会再用勾刺箭伤你们的心……就算不用此物,我国军队以后一样能反败为胜!为戏,还是杀着?听他的言语却是滴水不漏,仿是在堂上请求对方派人出来,仅供嬉戏玩乐,可众人都明白,如果今天不想办法打下乌木齐的气焰,等他回国之后,只怕两国又会再起争端。皇帝神色更是冷到极点,一连说了几个好,才淡淡地道:“不知王子,准备怎么为戏?”乌木齐王子浅浅一笑,他本来面色就呈小麦之色,脸上神色在灯光下一照,居然有些暗红,仿佛青年遇到心仪的少女,竟有些害羞的神色:“既是以勾刺剑为戏,自然得有人配合,臣下既然已与贵国修百年之好,臣下自是有如皇太后的子侄一样,我国虽无天朝如此繁多的礼教仁仪之防,但有一点还是尊崇的,既是尊卑已分,我父既已向族人承诺,让臣下拜了天神,按道理来说,与臣下为戏的,自是你国已拜天神之人,只可惜,贵国那人却是千金之子,不做垂堂”他轻轻一叹,眼波凛凛一转,“也罢,我国被贵国称为蛮夷,总是没有贵国那么多规矩的就勉强请宁王殿下陪臣下一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