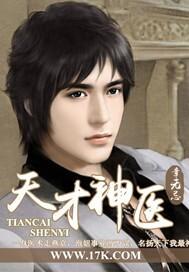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秤砣树根的药效能治肝炎吗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管乐上班很晚,从不在意流言,母女几乎只有在早上匆匆见上一面,然后各自分开。
即使她爱管乐,仍旧像个孤儿般长大,因为好像只有她生活在流言的世界里并从不肯承认自己对他人的眼光在意极了。
管平安为自己的懦弱而痛苦。而这痛苦让她成为一个看似冷漠的人。
她对苏留白冷漠,因为在他身上她看不见未来和希望,这是一个同样被畸形怨毒的情感禁锢的少年,他们无法分担各自的痛苦,更无法抚慰对方,只能将这种痛苦乘以二,那才是看不见的深渊。
管平安伸手将苏留白的眼镜摘下放到床边,然后也让自己侧躺,以便更近距离地观察苏留白平凡而惬意的五官。
他不是让人惊艳的男人,神情中总带着沉稳和不可动摇的温柔,但这温柔也是有限度和温度的,她知道他对许多不公平坦然处之,也知道他发起火来同样令人恐惧。
她从来没告诉他,以后也不会告诉他,从管家去往美国的路上,她因为见到一对父子而临时改变了行程。
华发苍老的父亲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脸上放心的笑容在儿子转过身后立刻变成了担忧和不舍,老人脸上那份挚真的情感瞬间凝结,那一刻,她想到了他。
苏留白这个少年,以为自己看透沧桑和未来的那种少年独有的单纯,会通过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模样,她很好奇,也忽然不舍和惦念。
在管家的三年,她喜欢上一个称作叔叔的人,接受命运而成为他的妻子变成了她人生的全部,但结局总是这样不圆满。
那些甚至刻意讨好的日子,她惭愧地以为自己忘记了千里之外的自己的孩子,而这一刻,短暂而漫长的人生旅途又将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她又想起他和他们,带着愧疚和牵挂。
她改道飞回这座城市,决定将自己的人生归回原位,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这责任里不包含苏留白。
她爱不起他。
管平安不愿自己像个外星来客似的接受众人的洗礼,她偷偷来到他的学校,打听到他已去了本市最大的医院实习。
门卫老人对苏留白这个在医大比明星还出名的学生所知甚多,在他滔滔不绝的嘴里她听说了那个学生如何带着孩子上学,如何起早贪黑地打工,每年竟然还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拿到奖学金……
管平安恍恍惚惚走出校门,来到那所体型庞大的医院,医院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迈着匆匆的脚步,带着一张麻木仓皇的脸。只有她,不知道何去何从。
&ldo;我他妈的杀了你。&rdo;一声怒喝,让步履匆匆的行人停了下来,随着他们好奇的目光看去,管平安刹那见到了那张熟悉的脸。苏留白被面前高大壮硕的男子猛推了一把,向后退了几步才停住,只听见那人喊道:&ldo;我救不救关你屁事,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今天他要死也死在你们这儿,是你们杀的他。&rdo;
&ldo;你说,他到底是不是你儿子?&rdo;苏留白没有恐惧,淡然地将歪斜的眼镜扶正,镜片下一双眼睛平静地望着男人。
男人冷笑,&ldo;是又怎么样,我没本事救,有本事你找他妈去啊。&rdo;他看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嘴一撇,继续说道:&ldo;他妈傍了大款,有都是钱,她都不管我管什么。&rdo;男子说完,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点了一支烟。
苏留白问道烟草的味道,皱着眉说:&ldo;如果你再不签字我就报警了,还有,这里不需抽烟。&rdo;说着,一把将男子嘴里叼着的烟按灭扔进了垃圾桶中,男子一愣,怒张了眼睛,脸上的横肉耸动间就扑了上去,他硕大的拳头在半空中落下,目标直指穿着洁白的大褂的苏留白,苏留白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围观人群蓦然一阵骚动,但无人上前阻拦。倒在地上的苏留白感到口腔中的腥甜,伸手摸着嘴角一看,果然已经流血。
&ldo;你到底签不签字?&rdo;他挣扎地站起来,依旧问那个男人,男人目光阴冷,&ldo;不签。&rdo;
苏留白微微一笑,&ldo;这个世上我最恨放弃孩子的父母。&rdo;说完,他将白大褂脱下整齐地叠在脚边的空地上,下一刻人猛地冲向男子,他动作迅疾勇猛,气势强悍,男子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人已经被他撞倒,苏留白骑在他身上,拳头狠命砸了下去……
这是谁,管平安看着骑在他人身上舞动拳头的男子,不敢相信这是她记忆里那个因为她被罚感到愤恨,却只感偷偷将那老师自行车放气的文弱的少年。然而下一刻,他果然还是他,纵然气势如虹,毕竟是文弱的书生,男子短暂的劣势被迅速扭转,他翻身骑在苏留白的身上,与苏留白花拳绣腿不同的铁拳头猛砸了下去,苏留白脸上身上瞬间就开了花。
依然没人肯出手,看热闹的人却越来越多,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令人厌恶的生动起来,管平安不能漠视这种单方面的殴打,她环视四周,在脚落里打碎玻璃抬出一个消防桶来,铁质地消防桶重量不清,她不得不的两手搬起,吃力地撑开人群来到纠缠中两人的身旁猛地冲彪悍的男人砸了下去,那人应声而倒,重重地压在苏留白的身上。
苏留白费力地推动他沉重的身体将自己移出,他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但此时地上只有轻轻晃动的消防桶。
周围的人群面目依旧丑恶,他们将苏留白团团围住开始嘘寒问暖,但苏留白满心不悦,他们将那人的去向遮挡然后扶起他,这种帮助他只嫌太多。
趋吉避害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勇于助人的人都是克服了这种天性的拥有强大的灵魂为肉体提供支撑,他和她都一再告诉自己,人本该是这样的。
管平安逃了,她害怕被拘留在说不清真相的地方面对不肯听真相的人,她更害怕以这样的形象同他见面,像那个被痛苦勒紧脖子难以呼吸的夜晚。
回到仍属于那个夜晚的房子,空气中洒满灰尘,窗外月光下,树影张牙舞爪摇晃的影子落在墙壁,好像无声惊悚的影片。她没有开灯,怕让人知道自己回来,怕他闻讯找来,换了干净的被单,她窝在床上墙壁上的影子回忆着过往,沉沉进入梦乡,竟然一夜无梦。
第二天,她揣着一张入学通知书飞往美国。
那张通知书是她在管家唯一的成就。
飞机上她手里一直握着一张照片,直到照片被死死攥紧的手浸湿扭曲,她才猛然回神放开,露出那张微微泛黄的照片,里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皮肤上带着不健康的青紫。
孩子正张大嘴哭号,或许已经预知与他的人生有着莫大牵扯的某人将会将他抛弃,苏留白说他最恨放弃孩子的父母,她何尝不恨这样的自己,又怎么能带着这幅嘴脸出现。
然而在某些时候,爱恨都不再重要,她就这样平静地看着苏留白的深沉的睡着,轻轻发出的鼾声也不讨厌,她管平安甚至想如果两个人就这样过完一辈子也不算冤枉,可她心里混乱的思绪和沸腾的情感总在纠缠撕裂,无比嚣张地叫嚣着它们的存在。
她慢慢伸出手指,顺着苏留白脸颊的曲线轻轻刮。他睫毛微动,没有睁开,她却惊诧地缩回手,如同每次克制自己放松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