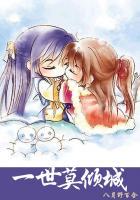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驯龙师音魂 > 第113页(第1页)
第113页(第1页)
容幽顿时寒毛倒竖,说:“我们都两个老人家了!能不能别这么色情……”“这要怪你,明知道自己老了,为什么还保持这么可爱。”谛明叹了口气说,“麻烦你躺好,不要再来卖萌了。如果我吃了你,勿谓言之不预也。”容幽于是知道,他还是顾及自己的老毛病。换在十年前,小明叔叔岂有先行警告的道理,都是反过来先装绵羊,熄了灯才会露出狼尾巴来。夜间,容幽恍惚间做了个梦。他夜半惊醒,在黑暗中沉思了片刻,见到身旁的谛明还在沉眠,便悄无声息地下了床铺。这些年他也习惯了屏退寝殿中所有宫人,此刻只能独自摸索着找到鞋,向外走去。他找到书房,只小心地点亮了一盏灯,并取出一张圣旨——以纳米纤维制作、能够储存上千万年的纸页,在上面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送行6221年初秋,容幽登基以来,大朝首次被中断。因为皇帝再次病倒,这一次情况并不乐观。御医处通宵灯火,世界各地的顶级医师被一齐征召,帝国各地军事活动暂停,贵族寄子全部召回龙卫二,皇宫禁军彻夜待命。几位阁臣住在偏殿,按律为君王守夜,因为年纪都不老,所以还能撑得住。皇帝不让任何人侍疾,只肯听御医的吩咐检查和吃药,身边只有一个宫廷行走在照顾。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最重要,所以没有任何人提出意见。容幽开始通体发烧,龙鳞偶尔在颈侧出现一会儿,心口的疼痛变成了一件令人习惯的事,甚至没有再引起他的注意。他日日夜夜地做梦,时常梦见一些过去发生过的事,还有曾经以为会发生的事。他恍惚间也梦到过自己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注册驯龙师,然后偶遇了只手遮天的明亲王,又和他谈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醒过来的时候,他对床边的谛明笑道:“你为什么怎么都不肯放过我?”接着容幽意识到床边的谛明没有戴面具——自己还是在做梦,梦到的是当年的明亲王。而明亲王站在龙血形成的血泊中,说:“小幽,为什么你对天下都温柔,只对我一个残忍?”容幽于是又惊醒,这回是真的醒了。床边的谛明捏着他的手腕,说:“又做什么噩梦?”容幽虚弱地说:“你又把我吃了。”谛明戏谑道:“不是美梦吗?”这时的容幽已经没有精神和他吵嘴了,只是侧躺在枕头上,眼神专注地看了他一会儿,说:“给朕端茶递水来。”谛明起身给他喂了两口水。容幽一脸满足道:“我老婆从没有这样乖过。”谛明笑了起来,也没有反驳他,说:“我帮你把项链摘了,睡了这么久,也不嫌硌?”他指的是容幽一直贴身挂着的项链,上面串着两人各一片护心鳞。容幽的黑色龙鳞很小,而谛明的青色龙鳞又大又亮。容幽说:“不给你,我要带走。”说完,他也意识到自己这句话充满了死气,便补充道:“等你不在的时候,我要藏起来的。”正午时候,谛明是不在的。因为外面轮值的阁臣会进来给皇帝读一天的奏章,汇报一下帝国里发生的事情,顺便侍个疾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今天轮值的是财政大臣傅定,他也是皇帝的老朋友了,坐在床边翻了翻内阁准备好的文书,说:“全都是好消息,陛下想要听哪个?”容幽嫌弃道:“朕都做了二十多年皇帝,还当朕是愣头青。这种东西,不听也罢。”傅定便在床边静静坐了片刻,说:“陛下。”容幽等了一会儿,只感觉头晕目眩,还是没等到傅定要说什么,便道:“什么?”傅定走上前,将容幽扶起来一些,然后半跪在床沿,用毛巾为他擦拭鼻血。这时容幽才意识到自己在流血,说:“没什么感觉,叫御医吧。”御医很快来了,同时来的还有几位皇室成员。容禹来得最快,甚至顾不上风度礼仪,三步并作两步地到了皇帝床前。这时候的容禹也成年已久,为皇帝分担过不少政务。这些天皇帝病倒的时候,主持朝政的便是容禹。按律,他身为皇太子是可以在御座上主持小廷议的,但他坚持坐在御座的下手位置,表达自己仍是皇帝的臣子在做事。可惜这时,皇帝已经昏睡了过去。容禹静静坐在床边,目光自然而然地流露着悲伤。而他妹妹容岚已经哭得不行,只能躲到侧殿去避开人,因为皇帝向来疼爱这个小女儿,从不舍得看她流泪。长公主轻轻伸手放在容禹肩上,说:“人皆有时,你要做好准备。”容禹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侧过头去看御医。只见容青和御医站在一处,听完御医们说的话之后,眉头紧锁,再没有舒展开。容幽在迷蒙间突然醒了几次,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可能命不久长了。第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御医不得不用药叫醒他,竭力继续进行诊断和抢救。趁着这个机会,容幽又召见了几名阁臣,各自吩咐了一些事。其中,他的潜邸之臣方存仁年纪尚轻,跪伏在御塌前,哭得不能自已。对他而言,眼前的皇帝是相马之伯乐,一手将他自贫寒中带起,又引领着他实现共同理想的明君圣主。皇帝逝世,既代表着自己失去了二十多年来的信仰,也代表着一个黄金的为臣时代的终结。“人皆有时。”皇帝沙哑地说,“方卿,好自扶持新帝。”方存仁再次顿首,哽咽道:“是,陛下。”方存仁走后,皇帝召见的是封英。自从容青醒来之后,皇帝便一直刻意避开封英,现在弥留之际,终于也不得不再见一次故人了。皇帝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首次仔仔细细地告诉了封英,并说:“那时只觉得对不起你。现在想来,还是你比较聪明,忘却一切后,活得那么轻松。”封英眼中含泪,说:“既然如此,陛下又何必还要告诉臣呢?”皇帝说:“因为我突然想得很明白了。封卿,逃避痛苦是可以的,但你不应该逃避一个爱你的人。好好和皇兄说会儿话吧,他不会强求你回心转意,只是想还能偶尔见到你——就当作是朕给你下的最后一份诏书了。”封英叩首,说:“臣领旨。”容幽的第二次醒来,是在深更半夜,他甚至不确信自己是不是真的醒了。他首先见到了艾丽希公主,便说:“你果然是……突破了第二阈值。”艾丽希公主也在哭,并说:“陛下,有人想要见您。”容幽这些天见到的眼泪实在也是够多的了,闻言后问:“谁?”他问完,突然见到了一个身影——这些年来魂牵梦萦,都未能一见的身影。白瀚坐在他床边,替他掖着被子,说:“小幽,你长大啦。”容幽怔住了,凝视着白瀚一成未变的颜容,说不出话来。白瀚微笑道:“傻孩子,我是教你怎么活得坦然而轻松,不是让你这么拼命。做错了事就做错了事吧,来爸爸的怀里哭一会儿。”他抱了抱瘦骨嶙峋的容幽,这个怀抱的温暖几乎让容幽以为一切都是真的。接着,床边又走过来了容娴,说:“我的小幺儿,才不是傻孩子。”容幽低低地叫道:“妈妈……”话一出口,就像所有的寻常梦境会被自己的动作打断一样,容幽突然无比清醒,睁眼就看到了熟悉的房间。床边,谛明看着他道:“梦见了谁?”容幽忽然喉头哽咽,眼前有些模糊地说:“很多人。小明叔叔,你快让我梦回去,我还没有见到霜楼。霜楼为什么不来见我,是因为对我很失望吗?”谛明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说:“也许他对一切都很释然,已经转世去了。”然而辗转梦回,容幽也再没有见过他们。容幽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阁臣们几乎都到了偏殿。又轮到傅定守夜,这说明容幽不知不觉间已经昏睡了整整一周。而谛明就站在床边,这是违反礼仪的,但是傅定好像看不见他一样,并没有说一个字。容幽意志清楚,但口舌吃力地吩咐道:“傅定,遗诏在……书房。”傅定说:“臣知道了。”容幽又眯起眼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怎么……还是不肯好好染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