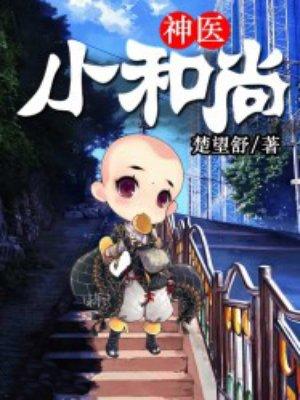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下粮仓酒42度多少钱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孙敬山抹着汗:“该……该杀!”
卢焯猛地转身,厉声:“不!该让他说出打闷棍的缘由!”
18.米镇街面上。夜。
空无一人的街面独行着米河。泛着青铜般光泽的石板路上,落着一条长长瘦瘦的人影。米河在人影前站停了。他是卢焯。
“是你?”他认出了这人是牢里为他搓草绳的男人,高兴地笑了,牙齿在月光下闪着亮,“你也出牢了?”
卢焯把两只手伸出,手掌上全是血迹。
“你挨打了?”米河惊声。卢焯:“一百二十板。打完了,被赶出了牢房。”
米河:“你真的偷东西了?”卢焯:“偷东西的手,会搓绳么?”米河笑起来:“这倒也是!——对了,有句别人留给我的话,我想问问你。”卢焯:“既然是别人的话,为什么要问我?”米河:“我看得出,你是个肯帮我的人!”
卢焯轻轻笑了:“问吧。”
19.石拱桥上。
卢焯:“……那和尚就是这么说的?”
米河:“对,就是这么说的!”
卢焯在桥心站停了:“和尚不是要你去讨饭。”
米河:“他既然不是要我去讨饭,为什么要把空钵交给我?”
卢焯看着米河:“你真想知道?”
米河认真地点头:“想知道!”
卢焯:“和尚是要你去救人!”
“要我去救人?”米河一惊,“他要我去救人?拿着这只空空如也的瓦钵?”
卢焯点了点头。米河:“可他……可他要我去救谁呢?”
卢焯:“救天下该救之人!”
米河震动:“救天下该救之人?”
卢焯目光灼灼:“天下有多大,你手里的这只瓦钵,也该有多大!”
米河的心狂跳起来:“天下有多大,我手里的这只瓦钵,也该有多大?”
“对!”卢焯的声音被风吹得很远,“因为,你捧着的是一只天下人的饭碗,大饭碗!”
米河近乎痴迷了,哺声:“我捧着的……是天下人的饭碗,是天下人的……大饭碗?……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说得多好……”他从怀里掏出瓦钵,看着。
桥下,河水在默默地长流。河风吹得桥柱上的风灯一明一灭。
“你是谁?”米河突然想起什么,回脸问卢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