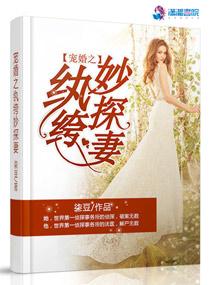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糖颂甜品怎么样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那天她和诗咏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按照惯例在画室碰头。自画室装修好后,这就变成了她们默认的主要活动点。
她到的时候门还开着,她走进去发现没人,就坐在桌子边等,等了许久人还没到就开始自言自语。她向来没什么耐心,不多久就起身打电话,才知道诗咏还没下班,约摸还要半小时。
她无奈,正准备先去影院,却在转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木箱。她吃痛,扶着箱子摸自己的膝盖,弯腰时,竟然看到唐颂坐在窗边画画。
她揉了揉眼睛,确定没看错,才直起身来。
他一直在这?自己发出这么大动静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正想叫他一声,唐字的发音竟在唇角绕了几圈消散开去。
他好像太过专心,专心得让她不舍得打扰。
她记得那天夕阳灿烂。窗外是金黄的银杏,阳光倾斜着洒落进来,将这半边屋子分成两块。唐颂就坐在阴影里,面前是画布,身后是几个堆高的箱子。
甘棠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却在那一刻无比感激它们挡住了她的视线,也挡住了他的视线。
甘棠看得有些痴了。
半边明朗半边暗沉,他的侧脸在光线的衬托下显出英朗的线条,整个人是那样沉静。
她看过他摆弄镜头的样子,见过他翻看影集画集的样子,那都是认真而细致的,用一句很老套的话来说就是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她对魅力这个词始终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可是这次,她好像能把魅力具象化了。
因为他那样沉静而专注,好像对面的画,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甘棠的视线顺着他的侧脸移到他的肩膀,然后是手臂,再从腕骨到那瘦削而有力的手指。
他也成她眼里的一幅画。
也不知看了多久,直到他侧头发现了她。
甘棠心虚,想被戳了一下,忙解释说是来找诗咏,脑子里却全是打扰了他创作的惶恐和不安。不过很快,这点不安就荡然无存了,因为唐颂竟然一边画画,一边有意无意地找话题跟她聊天。她木木地听,时而接几句,又开始纳闷难道他画画都不用专心致志用脑子的吗?
算起来,那天下午是他和唐颂第一次单独相处,没有诗咏在场。
和她莫名其妙的紧张相比,唐颂显得自在许多。
许是没有特别必要的东西可以聊,但又不想让气氛冷下来,两个人一来一去竟然扯到了油画上。为了不暴露出自己的无知,甘棠绞尽脑汁地搜索起中学美术课本上的内容,什么立体派野兽派,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打算扯些专业名词来装一装,结果还是只能想到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梵高的向日葵和星月夜,还有达芬奇的鸡蛋,根本没什么含金量。
他也没深究,只随意地问最喜欢哪个画家。
她腆着脸,思索了一会儿说:&ldo;莫奈。&rdo;
他看了她一眼,问为什么。
她只好干笑,找不出理由,或许只是因为在达芬奇的鸡蛋过后,她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幅幅的睡莲。
守着同一片睡莲,能画出那么多幅画,够无聊也够水平。
然后,她就听见唐颂淡淡地说,在他心里,莫奈更像一个孤独的骑士。
她插不进嘴。
一般人说这话总会有点卖弄的意思,但甘棠知道他不是。
因为他用一种很郑重的语气说,作为印象派的先行者,莫奈所克服的困难远比那些昙花一现的画家要多,而他又不退缩,反倒一往无前。他很欣赏他的勇气和坚持。
不知怎么,甘棠竟然听出了一点淡淡的感伤。
&ldo;很无聊是不是?&rdo;他笑着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