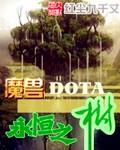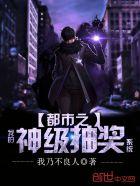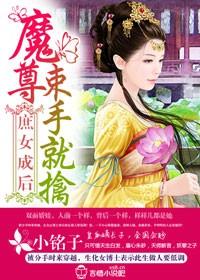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红楼之宁府新贵 > 第二百九十九章 自乱阵脚(第2页)
第二百九十九章 自乱阵脚(第2页)
正当此时,内阁大学士叶百川又站了出来。
“陛下,九边事关国之安危,军中糜烂至此,不可轻视,请陛下明旨,彻查此事。”
百官对于叶百川摆明立场的支持,反倒不以为奇,谁都知道,这位大学士盯着军中已经很久了,上次想要借新设备倭司之事,便与对军中加以整治,想要裁撤冗兵,却被朝臣联合反对,不了了之,此次怎会轻易放过。
傅东来也看着这位同僚,改革军制,记得在他出任吏部时,就已经提出过一次,可惜那时新政底子薄弱,他不能看着新政还未开始,就为自己竖起一个强大的阻碍,是以后来自己也多次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直至几日前,他依旧反对,昔日意气相投引为知己之人,渐渐形同陌路。
今日他却不再反对了,新政三年,根基已经扎下,是时候动手了。
想要进行军制改革,不剪除盘亘在路上的勋贵这条拦路虎,岂能成事?
大乾的两大根基,一曰政,一曰军,他要两手都抓,不然新政就如空中楼阁,这也是当初皇帝选择他的原因。叶百川是干臣能成,可于大局还欠缺了些,这也是当初为何是自己举荐他,而不是他举荐自己的原因。
一旁的叶百川,见傅东来没有出面反对,心中同时松了口气,他的入阁之路坎坷了些,足足两次才得以成功,这还是皇帝力捧,可直至如今,还有人说他是幸进。
虽然在他力主之下,大乾在辽东扩土百里,可毕竟比不得傅东来接连搬到两位辅臣,扫除了宣隆朝留下的腐朽之源,于百官来的更深刻些。
内阁四位大臣,排名在最后的一人是顾春庭,资历浅薄,自然无法与前面三人相争,而他却排在第三。
傅东来的能力和资历,叶百川都是心服的,可杨廷敬,宣隆朝留下的最后一块儿残渣,除了上朝打瞌睡,派皇帝的马屁外,还会做什么?既是新政,那就该人人为先,留着这样的人做什么。
说白了,他想做事,如果能凭政绩更进一步,谁又会拒绝呢?
已经准备致仕的冯恒石,人在班列中,看着昔日的两位好友,心中一声哀叹。
官场上,哪里有永远的朋友,今日之事,他如何看不出来叶百川未曾与傅东来商议,越过如日中天的次辅,为的哪般,傻子都明白。
怪只怪,傅东来压的叶百川太狠,当初傅东来保举叶百川入阁,看似恩遇,可叶百川首次势力何尝不是受了他的影响,偏生傅东来还争不过杨廷敬这个活泥塑,偏生叶百川也是一位想要干事的能成
许许多多的偏生聚在一起,注定了两人无法在形成昔日的联盟。
别人不知,冯恒石却知晓,大乾许多南方籍的将领,已经站在了叶百川一侧,他们是军中新兴的一派,既不靠开国一脉,也不靠宣隆一系。
朝会上,皇帝并没有当场下旨。
毕竟牵涉九边,百万大军,不得不慎,虽然皇帝心中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是谁想要自己的性命,可该矜持的,还是要矜持,哪怕只是做给勋贵们看。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皇帝自己等不及,频频派御医去催林如海,可偏偏事到临头,他却又要立牌坊了。
可想明白了皇帝的立场,也就不觉的奇怪了。
对此,无论是林如海还是贾瑛都已料到,所以,傅东来才没有开口。
往日朝中反涉及大事,都是傅东来力主,叶百川附之,首辅杨廷敬无论对错,都会与傅东来反着来,顾春庭则是那个听命办事的人。
朝臣们,甚至已经总结出了规律,只要是傅东来力主,杨廷敬反对的,基本都能成,这次两位都没开口,那事情就还要等。
等什么,谁都不清楚。
散朝不久,绣衣卫指挥佥事沉翔便匆匆入宫,呈上了林清的供词,宫中传出消息,皇帝在华盖殿大发雷霆,砸了好些珍奇古玩名砚,可依旧没有下旨彻查。
散朝回衙的路上,贾瑛明显感觉身边熟悉的身影少了,似乎都在躲着他走,一些在京任职与贾家交好的勋贵,更是毫不吝啬的留下冷脸,翁婿二人的略显孤单。
西平王府。
史鼎、陈文瑞、候效康还有几家公侯伯府的主事人都聚在这里。
“侯爷,你说这事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是啊,侯爷,咱们在九边已经一退再退,他们这是要干净杀绝,更关键,家里还喂了一直养不熟的狼,咱们决不能就这么算了。”
众人此起彼伏,蓝田玉心中却在冷笑。
这些人怕是在北王府吃了瘪,才找到他的门上,想让他做这个出头鸟。
“诸位,我等四王八公之家,一向是以北王府为首,长幼之叙不可废,诸位还是再去一趟北王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