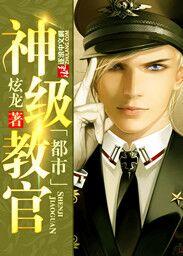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英雄无名 军统 > 第91章(第1页)
第91章(第1页)
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
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大体上对我们都已有了交代,此刻天色已近黎明,大家也需要休息一下了。
鲁翘回房小睡,炳西兄预备就在椅子上坐一会。戴先生招手唤我到他房里去,大概是有事单
独和我谈吧?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
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我问戴先生:「对汪的工作,
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戴先生两眼望着我,
但不作答。于是我又追问了一句说:「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戴先生略作考虑,
他回答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
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我明明知道无须多问了,可是耐不住性子仍然再问了一句,我说:「此地的工作告一段
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因为我的职务在天津,家小也在天津,理当有此一问,殊不料
却惹出几句闲话,他扳起面孔瞪着我说:「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这又从
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我心里好
气!
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我想回天津,是眷恋家小,干我们这种工作的,又际此
战时,如果没有家室之累,免去许多牵挂,那该多好!不过,这是属于理智的、工作上的谅
解,谈到私情和人性,摆在谁的身上都会感到不快;何况我又是一个不大有含蓄的人,既然
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
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
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先生交代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
和他的爱,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