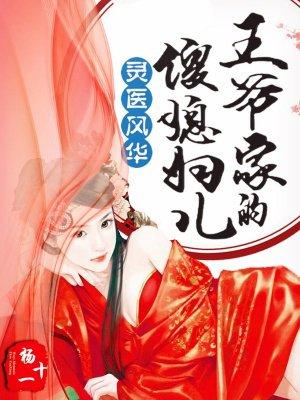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谋宫心计 > 第162章(第1页)
第162章(第1页)
锦衣没再出声,垂着脑袋跟着侍卫陪着皇上一起进了延寿宫。皇上先入了殿,与太后说了几句后,锦衣才被宣召进了殿内。
殿内燃着提神的香,太后手里拨着一串念珠坐在正手的大椅上,旁边便是一脸闷色的顺帝。
锦衣恭敬的磕头行礼,将才被平身,就听到太后沉着嗓音问到:“锦贵人,你不是不适吗?怎么有精神去了贵妃殿里?”
“回太后的话,锦衣回到殿里后,思及贵妃一人在殿内过节,只怕孤单,便想过去陪陪,故而去了。”
“为何只你一个过去,连个丫头都没带?听说你还把春梅给支走,说你要和贵妃说说心里话,哼,不知锦贵人有什么心里话要和贵妃说的彼此泪流满面啊?”
锦衣闻言恭敬的颔首而答:“回太后的话,锦衣是告假归来的,若是直接过去,恐人议论说锦衣眼里不分大小,有不尊之嫌,便一人悄悄到了正殿。当时春梅正伺候着贵妃娘娘,锦衣见贵妃娘娘形容憔悴,实在心中不忍,便向与娘娘献上一家传的方子,好令她燃起希望,早日将息好身子……”
“家传方子?”太后挑了眉:“不知是什么方子?”
锦衣的脸一红,头埋的更低:“是,是调宫理身便于受孕的方子。”
太后闻言眼角微微一颤,而后有些似笑非笑的打量了锦衣好一会才说到:“想不到苏家还有这方子,不过皇宫里的太医们可不都是吃闲饭的,一个调宫的方子,你当他们就没有吗?”说着太后一拍桌子,手里的念珠恰恰断裂了线,霎时念珠飞溅,噼噼啪啪的散落了一地:“说!你到底和贵妃说了什么?”
锦衣立刻起身下跪,即便跪到了念珠上咯了膝盖,她也咬牙忍着撑着。
“说话呀,你到底说了什么,两人要哭成那样?嗯!”
“回太后的话,锦衣真的只说了方子的事……”
“来人,掌嘴!”太后不客气的吩咐了一声,立刻左右的两个丫头就要上前,身边的顺帝见状刚要制止。太后却看向了顺帝:“皇上!您可是答应哀家只看而不问不管的,今次的事,是由哀家来处理的!”
顺帝无奈只得落座,而此时只听到啪啪两声脆响,锦衣已经被两个丫头各扇了一巴掌。
“哀家再问你一次,你要是再不说实话,哀家就叫人把刑具搬来,就在这里用刑。你别以为皇上疼你,你就可以满嘴跑马,我告诉你,哀家处事最为公断。今日里不为贵妃讨一个公断,我枉做她的婆婆!”
锦衣的脸上火辣辣的烧,可人却并不慌张,她正了正身子,恭敬的对着太后与皇上磕头:“回太后的话,锦衣并未扯谎,当真只与贵妃说了那方子的事……”
“啪!”剩下的半截念珠被太后一把甩到了锦衣的面前:“你这丫头倒还嘴硬,你当哀家和你说笑吗?来人,去取刑具来!”
“是!”殿外有太监应了声而去,此时顺帝急的脸色都白了,忍不住小声说到:“母后,有什么不能好好问呢,何必一定动刑?锦衣说只说了方子的事,兴许就只是说了方子……”
“皇上的意思,是哀家武断了吗?”太后说着一摆手,一旁的柳儿立刻打开了角门,当即,春梅与蔡宝还有孙太医鱼贯而出。
“皇上可以问问她们,如果您觉得春梅的话不足信,那蔡宝呢?孙太医呢?他们可是都看见锦贵人一脸泪水的从正殿跑回到含香殿。”
顺帝闻言立刻扫向这三人,当下三人都是下跪行礼确认他们是见了锦衣挂泪而归的。
“锦衣,你到底和贵妃说了什么,你快说啊!”顺帝有些不安的看向了锦衣,可锦衣却是抬头看着他咬了唇:“皇上,您别为难锦衣了,锦衣确实只和贵妃主子说起了方子的事,虽然事后贵妃也告诉了一些话给锦衣知道,但锦衣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朕叫你说!”顺帝紧攥着拳头盯着锦衣,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令锦衣这般闭口不谈。
锦衣咬了唇,只管磕头却不说话。此时殿门拉开,几位太监鱼贯而入,夹板,藤条纷纷出现在大殿内。
顺帝的脸一下就白了,他刚要吼他们出去,太后却先拍了桌子:“来人,给她上夹板!她不是嘴硬吗?我看她说不说实话!”说着太后竟闭上了眼。
锦衣的心砰砰跳着,但是她面上却是一副要视死如归的模样。当夹板的绳板套上手,当左右两个太监开始分列而站的时候,她扫了一眼孙福兴。
“用刑!”
“慢!”
与太后同音的一个慢字,却是两人发出的,一个是顺帝,一个是大步而出的孙福兴。
太后诧异的看了顺帝一眼,眉头微蹙,继而转头看向孙福兴:“孙大人喊慢?是何因由?”
孙福兴跪在地上,颔首而答:“启禀太后,臣可能知道贵妃和锦贵人说了什么。”
“嗯?”顺帝闻言发出诧异之声,当下有些激动的说到:“你知道?”
“回皇上的话,臣有一发现一直难以开口,但这会的,臣觉得若不说出来,只怕锦贵人带其受过也不能了了这事,所以臣……”
“孙太医,有什么你就说吧!”太后微微翻了下眼珠子,依旧闭了眼。
“是。”孙太医说着看了下殿里的人,似有些犹豫,但还是大声的说了起来:“臣为锦贵人看过脉象出来的时候,迎面正撞见贵妃娘娘浑身是血的回来,当时臣吓坏了,以为娘娘受了什么伤,正要问,便听见杀人的事。贵妃娘娘不避臣的进了殿,稍后就有侍卫守门,臣进退不得,看见娘娘浑身是血,便还是抖着胆子进殿问娘娘可曾有伤,娘娘没理会臣,叫臣滚,臣便只好退出,但毕竟撞上这事不敢走远,便一直在角门恭候,后来,贵妃娘娘自尽,皇上叫太医,臣这才再度进殿,可贵妃娘娘已经无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