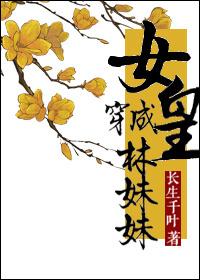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夜话聊斋类似的游戏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远远的是谁也在听这首曲子?
窗外下了雨,细细索索地敲打在梧桐叶上,敲得我一路心碎,碎成粉末在雨里飞。这样的夜里,没了爱人的怀抱,该是怎样残忍的事?
努力地蜷缩着身躯,怎么也无法入睡,透过薄光看窗外斜飞的雨,谁在谁的怀里?谁还在一个人街头买醉?
电话在床头忽然惊叫起来,刺耳突兀,响个不停。我用被子蒙住脑袋,我不想听任何安慰,不要。可是我敌不过它的诱惑,电话线里仿佛有林尚温柔的手指,轻轻牵扯我的神经。
努力地抬起沉重麻木的手臂。
&ldo;默默,林尚出事了!&rdo;
赶到医院的时候,林尚已经进了手术室,林尚的死党治青很严肃地问,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知道怎么了?
他喝多了,出来时被车撞了,天黑路滑,加上他突然闯了出来。
再见林尚竟然是满头的刺目的绷带,林尚的母亲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打开我扶在担架车边的手,和护士一起推走了林尚。
你爱他是吗?那你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在夜里游荡?一个人在酒吧里买醉?治青看着我很是不满。治青,你不要问了,不要,我慢慢倒了下去,鱼一样地滑到冰冷的水泥地上,有殷红的血从下身慢慢溢了出来。瞪着一双苍白的死鱼一样的眼,漠然地看向天花板,那儿有一只苍蝇,一只用细腿轻轻抖动翅膀的苍蝇。
治青提着一个食盒从门外走了进来。林妈妈让我问,你那孩子,是林尚的吗?
我忽然就笑,大声地笑,笑声里苍蝇跌落到雪白的被单上,黑黑的,还是一只苍蝇。
差一点就没了孩子,真的,差一点。治青的脸严肃地可笑。
林尚都可以离开我,孩子还有什么用?那会是林尚的孩子吗?会吗?我疯狂地笑着,笑得发不出声音,笑得流出了泪。
张着嘴,我感到我吞下了那只苍蝇,它已经进到我的胃里,在那里散播下足以让我腐烂的病菌。
吃一点吧。很老实的治青,用羊一样的眼睛,很痛心地看着我。
你可知道我心里的痛,你可知道?!
我闭上眼,连同回避这个无法用思想来覆盖的男人。我不想让自己清醒了,不想。
那个多事的夜晚,混乱的生日排对,晃来晃去的人,红的世界,白的嘴唇,跌撞的,拥抱的,还有……
我用最冷最冷的冰,想冻死那只苍蝇,真的,一切都不曾发生,一切却发生了……
林尚一巴掌打醒了我,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很无辜地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干什么?!
干什么!你看看你在干什么!林尚脖颈上的青筋都要暴跳出来了。眉毛竖着,脸色铁青,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恐怖的林尚。
忽然感觉出不对劲,低下头,身上竟然衣衫不整,旁边,天哪,躺着一个半身赤裸的男人!不是林尚,是治青,他竟然还在酒醉中,口边流着哈拉,勿自呼呼大睡。
发生了什么?我和治青?
我记得昨天是林尚的生日,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开怀畅饮,我拿出了全身的武艺做了一桌子的好菜。我记得我好像喝多了,然后好像倒在谁的怀里,我模模糊糊记得是林尚,他吻我,他轻轻地抚摸我,然后把我抱上了床,怎么会是治青?
治青端了碗,轻轻地吹去热气,我,我喂你吧。
我一挥手打翻了那只搁到唇边碗,那只苍蝇,汤撒了,撒了治青一身。
你怎么可以这样!林妈妈刚刚好看到这一幕。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弄撒了。治青一边慌乱地收拾破碎的碗片,一边惶恐地辩解。油津津的汤滴滴答答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流到他的整洁的白色衬衫上,沾污了一大片。衣服脏了可以洗,人脏了呢?
治青,你帮我照顾林尚吧,不要理她!林妈妈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掉身而去。
我去去就来。治青很狼狈地退出。我和林尚都努力地想忘记那个夜晚,我们和往常一样手拉着手卖菜,手拉着手逛夜市。曾经在车上看到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妻,肩并肩坐着轻声地聊,两人的手始终紧紧绞缠相握,平淡无奇的面容,朴素暗淡的衣着,脸上的微笑却那样的踏实温暖。我羡慕的对林尚说,我们也要一辈子牵手。
男女之间的飞跃通常都是从牵手开始,我们从牵手收获了爱情。不管风或者雨,仍然希望,牵着的两只手,是相通的两颗心。我怀孕了,林尚,会是你的孩子吧?我的声音小如蚊蝇,我知道我是不该问的,可是不甘心,不甘心啊,三年的恋情,三年的苦苦相恋,却被一个罪恶的夜晚给毁了。手牵着,心却不再相通。
林尚不说话,勾着头。狠命地吸着手里的烟,烟雾里,我看不清林尚的表情,我多么希望林尚说,不管是谁的孩子,我都会好好待他。
林尚?
不要问了!不要!林尚如一只受伤的野兽窜出了曾经一起苦苦经营的家。
要打麻药吗?
不用。
疼痛,刻骨铭心的痛却又那里及得上心口上的痛。白色的床单上留下了我的血,留下了那个无辜的未见过世面的曾经的小生命的血。
一切都成了回忆,一切如此的不甘……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我踏上了流浪的路,从一座城市影子一样的晃进另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