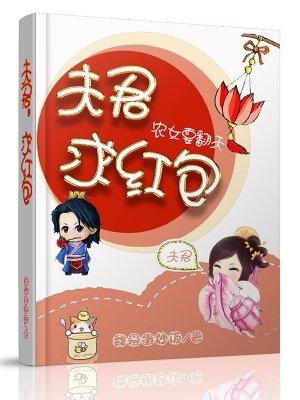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落花辞树虽无语 > 第120章(第1页)
第120章(第1页)
左相府,南院
南隽墨发披肩,只穿着件素色单衣,双眸如枯井般站在窗边,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短短一日,他竟觉得已经过了千百年一般。他迷茫的看着窗外明净的积雪和那些已偷偷钻出鸟巢觅食的雀儿们,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从哪里来,为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往哪里去。
他心中存了十年的净土,终究是被那冰冷的铁犁,无情的破皮起土,再不复存在了。
徐氏满目心疼,正站在他身后,拿着把木梳,沾了清水,细细的为他梳理多日未曾打理的墨发。
南央腿伤未愈,拄着拐杖站在南院门口,遥遥望着迅速消瘦下去的儿子,心痛如绞。
南福抹着泪道:“老爷,公子他会想明白的,您别再伤神了。”
南央形容枯槁,鬓边几丝白发被风吹的贴在脸上,忍不住泛起泪花:“因果报应,我活该如此啊!我现在不求他能原来我这个失职的父亲,只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
南福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家心高气傲、玉树风流的公子会变成这副模样。一听南央这么说,也有些伤感:“老爷,这世上哪有真的怨恨父亲的儿子,您这样子公子要是听见了,该多伤心。”
南央痛苦的叹了口气,不知该怎么面对身心俱伤的儿子。
这时,守门的家仆匆匆来报:“相爷,外面有个少年,自称是公子的朋友,说想要见公子一面。”
“朋友?”南央眉心一跳:“可是穿着一身黑袍,手中握着把长剑?”
那家仆暗道老爷真是神人,连声道:“不错,是这个打扮。”
南央沉吟片刻,却吩咐那家仆:“你去告诉他,公子身体不适,这几日不方便见客,让他速速离开罢。”
家仆虽不明白为什么,也赶紧应了声“是”,准备去门口将人打发走。
谁知他刚转身,院中便想起一声低哑的少年声音:“不必了。”
南央认命般叹了口气,挥手让南福和那家仆都退下,才看了看不远处仗剑而立的黑袍少年,黑着脸道:“这种时候,殿下应该避嫌才对。”
九辰脸色有些苍白,这么冷的天,只穿着件黑色单袍,也不见瑟缩。许是常年习武的原因,他站着时背脊异常挺拔,被黑袍一衬,整个人都显得很单薄。
闻言,他浑不在乎的笑了笑:“我从府后翻墙进来的,没人看见。”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近来对儿子太过愧疚,南央觉得自己这份为人父的心软,也蔓延到了别家孩子身上,有时在街边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乞儿,也会有想要堕泪的冲动。因而看见九辰这副模样,便问:“殿下昨夜恐怕也被那剑气伤了吧?难道不需要养伤吗?”
九辰抿起嘴角,道:“无妨,一点擦伤而已,我想去看看阿隽。”
南央虽不懂武功,也知道被那么厉害的剑气罩住,绝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擦伤。可这事他毕竟管不着,身为臣子,他也不能太过逾距。事已至此,他也阻拦不了,便做了个请的姿势。
九辰点头道了声“多谢”,便举步进去了。
徐氏见九辰过来了,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收起木梳和水盆,先行回避了。
九辰进屋之后,却是把剑搁到地上,正对着南隽背影,撩袍跪落,郑重一拜,道:“对不起,阿隽。我很歉疚,那个人,是我的兄长。”
南隽木然的面部,微有动容,怆然道:“殿下何错之有?”
九辰眸底,是死灰般的平静,表情却异常认真:“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也很愧疚。”
“我不能帮你救江淹出来。此人十分顽固,复仇之心太过强烈,不论是为了巫国的安宁,还是为了端木族剩余三十六路商脉的安宁,江淹都必须死。”
南隽空洞麻木的凤眸,终于颤了颤,渐渐溢出刻骨的绝望。他疲倦到极致的合上眼睛,眼角,流出一道泪痕。
九辰说完这件事,也彻底松了口气,嘴角微挑,道:“江漓已被我安排在城外养伤。我会找机会,让他们父女见上一面。我相信,就算为了自己的女儿,江淹也会从容赴死的。”
南隽眼角的泪痕,愈加明显。喉头涌起的酸楚,几乎要冲昏头脑,令他站立不稳,努力咽了许久,他才能发出黯哑的声音:“多谢殿下。”
“你我之间,何须言谢。”
九辰轻挑嘴角:“王都已非久留之地,等江淹的事情解决完,你若想和江漓一起离开,我会安排。日后,你大可游历四方,以行商为乐,时间久了,这些事就慢慢忘了。”
把要说的事情简单说完,九辰便重新握剑站起来,对南隽点头为礼,准备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