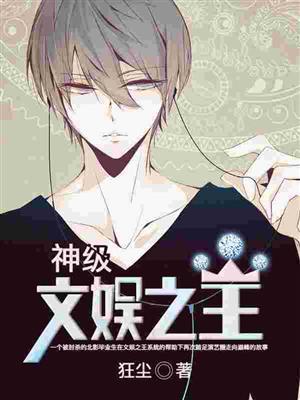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寒士风流 李显 > 第20章 抱大腿(第1页)
第20章 抱大腿(第1页)
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对于这个难倒了古今中外无数闲人的问题,蒋凝秋当然也是回答不上来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她一面吩咐路掌柜观察武云起在茶楼的一日活动,一面对着送过来的记录各种挑刺。
最后,这种无聊的行为连许愿灵都看不下去了。
“与其纠结于这些东西,还不如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件上。你现在简直像个跟踪狂。”
“是他送上门来让我跟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蒋凝秋用手指点着路掌柜送来的报告,理直气壮地回答,“在茶楼从早坐到晚,一连七八天都是这样。眼看着后天就是会试了,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不打算好好考了?”
“我记得你前世死的时候还没结婚?”许愿灵突然问。
“没结婚怎么了?”
“听你这语气简直像有孩子要高考了一样。”
许愿灵的比喻太形象,蒋凝秋竟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回去继续看报告。又扫了几行,她突然一拍大腿:“诶,你说他那天套我话,不会是打算通过我向太子那里走后门吧?”
我的目标一号不可能这么无耻!
“……你的脑洞有点大。”
且不论蒋凝秋将武云起脑补得有多么居心叵测,两日后,建宁终于迎来了三年一度、牵动大殷半个官场的科举会试。
之所以说半个官场,是因为如今大殷的选官制度,乃是由察举制与科举制双管并行。察举制承继于前朝,本意是考察各地的才德兼备之人,并将其举荐入朝廷,然而随着时日迁移,现已逐渐沦为世家子弟入朝为官的手段。为此,大殷朝第三代皇帝明宗周蔚另开科举,终于使寒门再度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直至今日,科举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会试是整个科举流程的第三级,应试者为各州通过了乡试、具有举人头衔的士子们。共三场,分别始于二月初九、十二与十五日,所试科目有明经、明法、明算等。三月十五日放榜,考中者再于四月二十一日参加殿试,定下最终名次,就此踏入仕途。
自从正月二十起,赶考的举人们纷纷来到礼部报名,整座建宁城就以比往常更甚十倍的程度热闹了起来。大小客栈人满为患,不少人家甚至将自己闲置的宅院腾出来,高价租给那些希望清静的书生们。书店的生意突然蒸蒸日上,文房四宝抢售一空,官宦家的孩子入国子监,富人家的孩子请西席,平民家的孩子进私塾,全城上下皆是一派“我有知识我自豪”的火热气氛。
这种热情在会试开始初日,几乎达到了。
“简直像狂欢一样。”蒋凝秋的茶楼离贡院并不远,只隔了一条街。坐在三楼的私人雅间里,她透过窗外看着街道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忍不住喃喃评价了一句。
“换了是我,便去考那武举,也来拿个状元当当。”蒋知秋坐在她身边,正对着一盘蜜汁鸡腿大快朵颐,腮帮子被撑得鼓鼓的,“不比这文举容易?”
“蠢材!”谢鼎深坐在桌对面,有模有样地品着茶。只可惜,面前堆叠的空盘子已经暴露了他刚才也在大吃特吃的事实。听见蒋知秋的话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发出嘲笑,说出来便觉得不妥,小心瞅了一眼蒋凝秋,见她没什么反应,这才续道:“你是侯爵之身,哪个敢考你?和那些寒门庶民混迹一处,成千上万人挤破了头,饿犬扑食般巴巴地抢夺几十个名额,说出去岂不是要满城权贵笑话!”
蒋凝秋听着这番话,只觉得有些刺耳。但谢家乃是大殷皇室之下的第一门阀,数代尊荣累世公卿,目标七号谢二少打小养尊处优,又本来就是狂妄自傲的性子,能说出这番话当真是一点都不稀奇。再说她自己也算是这个等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之一,更没有什么立场去谴责对方。
“二郎,慎言。”谢擎深开口,语气温和却不容辩驳,“寒门岂无能士,世家亦有庸才。如此目中无人,有辱谢家门风。”
“阿兄教训的是,我知错了。”谢鼎深天不怕地不怕,对着长兄时却会瞬间切换到乖宝宝模式,蔫蔫答道。
听听,听听。不愧是迷倒无数京城少女的一代大殷男神,思想觉悟就是不一般。蒋凝秋在心里给谢擎深点了个赞,却发现对方今日似乎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状态。于是问道:“伯襄可是有何困扰?”
“无事。”谢擎深向她笑笑,“只是有一位故人曾与我相约,今年参加科举。他应是早已到了京城,却不曾来寻过我。今日会试,我不免生出了些许记挂。”
“阿兄还有在外结识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谢鼎深好奇地瞅着他,“莫不是……当初在‘南巡’时认识的?”
逃离帝都流亡在外的那一年,对于皇家与王公大臣们来说,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皇帝与百官还朝,往后再提起那段日子,便都统一粉饰太平地称之为“南巡”。
谢擎深颔首,神情一瞬有点恍惚:“一晃至今,也有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