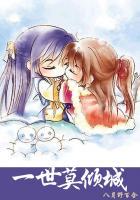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盗墓电影荒 > 第十四章 花访月(第1页)
第十四章 花访月(第1页)
今天晚上注定欣赏不到月亮,抬头望天,只能看见倏然划过天际的白色雷霆。
静安巡捕房前的路灯已经亮了,滂沱的大雨将原本明亮的灯火,渲染成了一片朦胧的昏黄。
这种天气里,路上已看不见一个行人,或许对有钱有势的人而言,下雨是一种调味剂,偶尔从室外的**,转换到室内的狂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对多数人而言,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其含义不过是多了几个时睡觉的时间。
总探长马正尧属于有钱有势的人,可失掉的血气,只能让他老老实实回家,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他确实是这番打算,并且已经叫了个姑娘在床上等他,不过事情的发展总跟预料的不同。
静安巡捕房的铁栅栏外,一身黑色雨衣的马正尧一脸严肃的站在大雨里,他看了看手表,表针已指到六三十的位置。这个时间赶过去,应该刚刚好。
他已不是当初那个身无分文,脚踩一双破鞋,从浦东过来的毛头子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硬是靠着赤水空拳打下了如今的地位,这上海滩里已少有能跟他对着干的人物,能威胁到他的就更少了。
可他今天要去赶一个饭局,一个虽不愿意,却不得不去的饭局。他理应一肚子的不满,但现在肚子里装的只有苦水和无奈。
丽都大酒店是他手下的场子之一,那已去过无数次的地方竟让他生出一种十分不适的陌生感。那里正有一个人在等他,而他也从主人变成了客人。
周围忽然一片大亮,他猛地抬头,眼睛捕捉到了一条即将消失的白色尾巴,紧随而至的是一阵隆隆的雷暴声响。这声音像极了钟声,似乎在提醒他时间就快到了。
马正尧不再犹豫,趋车出发。
丽都大酒店的紫竹居一个礼拜里只对外敞开一次,想要坐在这里吃饭,光靠钱是不行的,还得讲究缘分。这缘分就是抽奖,把一个礼拜来的预约名单用数字排号,抽中谁就是谁。
当然,这只是酒店自己的法。因为连续三个月里,抽中的号码,上面的数字均代表同一个人,这可比被雷劈死的概率还要多了。
想要来此附庸一下风雅的财主虽然怀恨在心,却也不敢声张。不就是吃饭的时候换个地方嘛,这总比被一个喜怒无常的公子哥惦记上要好多了吧。
紫竹居外,飞雨打竹叶,“瑟瑟”的声音听来并不刺耳,像是一种天然的伴奏,让这灯火盎然的雅居内,平添一股幽静的氛围。
紫竹居内,一位长袍缀金丝飘云图案的老人,正慢慢的温着一壶清酒。他目光平淡,似在注意着酒壶,又像在看着壶下的火光。
帘外窗前,大雨瓢泼,而在珠帘之后,却是一派安然祥和。
这时,有几雨从窗外飘进,落在了老人温酒的火炉上。
“嗞嗞。”待炉案上的水滴被蒸发干之后,老人对着空无一人的紫竹居幽幽叹道,“我为你取名枯叶,意味秋的萧瑟,秋的肃杀,秋的寂寥,这几样秋的品质,你至今仍未学会。”
淅沥的雨声,瑟瑟的竹叶声,温酒下火苗的燃烧声,老人等了许久,依旧没有等到第四道声音,那个躲藏起来的人,仍就像从前一样,不愿面对他的问话,对于这个结果,似乎并无意外,他只能转向另一个问题,“福源,现在何处?”
“华龙路,浮子行监狱。”声音是从老人背后传来的,可他背后却不见人影,而是一串珠帘,珠帘外种着紫竹。
“在这上海滩里,我琉璃厂的名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看来,拍卖行入驻上海的事情,的确是有这个必要。”酒已温好,老人倒了一杯,又问道,“可查清,福源为何会卷进这场命案里面?”
“并未查清。”这声音冷冽如冬。
“我看也不用查了,那胖子无非是觉得好玩罢了。”老人道,“与福源一同关入监狱的年轻人,他的身份查清了吗?”
“李清一,品古轩大少,上海四公子之一。”
“品古轩?”老人念道,这个名字他似乎曾经听过,可漫长的岁月已将他的记忆搅得很模糊,他也不记得是在何时听过这三个字。
一阵嘈杂的声响从门外传来,打断了老人的回忆,他不喜的皱起了眉。
“花少,紫竹居今天已被人包了,您就不要为难人了。我们已安排好了采香居,那里不比紫竹居差多少。这样成么,今晚花少的一切开销,统统免费。”
“上海滩谁人不知,这紫竹居一向为我而开。今天有人坏了规矩,我没有为难你们几个主事的已算客气,还想让我就此罢手?天下哪有这般好事?”
“花少,您别别……别啊,我们被上头关照过,这紫竹居今晚谁都不让进啊,求求大少爷您了,别为难我们啦!”
“哈哈哈,谁都不让进?好大的口气!里面坐着的是谁?莫非是马正尧?就算真是他,我来了,他还能安安稳稳的坐着喝酒吗?给我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