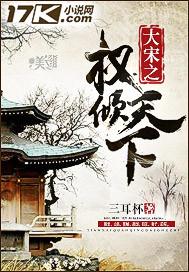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新安郡王见闻录书评 > 第一百八十章 故人再现(第1页)
第一百八十章 故人再现(第1页)
无论在何时,西市都是处处人潮汹涌。与达官贵人们常来往的东市不同,这里几乎见不到多少世家大族的宝马豪车,满目皆是各种各样摩肩擦踵的人们。乌发乌眼的汉人算是寻常,头发眼眸甚至皮肤五颜六色的胡人亦是随处可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市便没有能够入眼的宝物。来自大唐疆域之内的行商带来的珍奇,尤其是源自西域商路千万里迢迢送来的香料与宝石,足以留住所有人的脚步。西域胡商的豪富以及汉人巨商的奢侈,或许较之许多世家大族都更胜一筹。若非礼制所限,他们的吃穿用度甚至与王公贵族无异。
因为忙碌之故,李徽与李璟都有些日子不曾来西市了。二人跟在王子献身后,走入一家颇为别致的首饰铺子。店家见他们穿戴不凡,气度与容貌皆十分出众,立即取来了最好的玉佩、簪子等男子所用的饰物,又很是殷勤地准备好了茶水点心供他们缓缓挑选。
“店家再取些小娘子们喜爱的头面首饰来瞧瞧。”李徽道,“我们有位妹妹不日便要大婚,打算再送她些压箱底的首饰。”
店家自是喜出望外,忙又小心翼翼地端来好些乌檀木盒子。男子的饰物再珍贵,也比不得女子饰物那般用料繁多、精雕细琢。若是论起价钱,自然也是女子饰物贵上数成,所得之利就更不必说了。不过,说起来,这种贵胄出身的小郎君一般只爱走马长安,击球打猎,极少会亲自来铺子里给家中女眷挑选头面首饰。
店家所荐的自然皆是珍品,李徽端详片刻之后,便选了一套水头十足的碧玉头面。虽看起来并不艳光四射,但他觉得很称宣城县主温柔的性情。新安郡王虽对女子所爱之物并不了解,却并不妨碍他觉得甚么饰物穿戴起来更衬气度。
至于天水郡王,盯着那些盒子里的首饰看了半晌,苦着脸道:“阿兄,咱们不如直接送几百金给玔娘压箱?若是送首饰,她也未必会喜欢。直接送几百金,到时候她看中什么便买什么,岂不是两厢便宜?”
“……”李徽抬眉瞥了他一眼,“玔娘还缺这几百金么?送的不过是心意罢了。”堂堂宣城县主,越王府嫡出长女,自然不缺几百金的钱财。越王妃给她准备的嫁妆之丰厚,或许比之长宁公主明面上的嫁妆也只差上一两分而已。他们临时从西市上购置的这种好首饰,远远称不上给她压箱底,只能算得上是不错的礼物罢了。更精致的头面首饰,几乎不会出现在店铺里,早早地便送到各家府邸当中去了。
于是,天水郡王便挑了套错金红宝头面,看起来最为华贵喜庆。对于他的审美,新安郡王无言以对。王子献则微微一笑,也挑了两套看起来不错的白玉头面与宝石头面,又在他们二人并未注意的时候,买了一枚男子戴的羊脂白玉环佩。
他们匆匆而至,身上自然并未带多少钱财,也没有带上仆从,便只留下了名号,让店家送到府中去。听了濮王府与越王府的名字,店家不禁暗自抹了抹汗,悄悄给他们抹去了高价,不敢赚亲王府的钱。与两大亲王府相比,王家便很是寒酸不起眼了,但所买的头面首饰加起来也有数百金之巨,令店家与伙计均不由得为之侧目。
天水郡王也觉得好奇得紧:“子献,你若是有这么多钱财,怎么不买下正在赁的院子?或者干脆买更大的院子,离濮王府更近些?”他一直觉得王家是没落世家,家中应当有些清贫,却想不到他出手亦堪称豪奢了。
“身份与衣食住行应当相配。”王子献回道,“而且,家中确实没有多少资财。不过,这两样算是给妹妹准备的嫁妆。遇上合适的便给她们留着,免得日后再费心思寻。”他所买的,才是真正给王洛娘与王湘娘压箱底之物,也算是长兄的一片心意。
此外,他所言的家中资财,指的自然是王家的祖产以及小杨氏所剩下的嫁妆。小杨氏的嫁妆他并不打算动用,日后将王洛娘寻回来,便全部给她当作陪嫁;至于王家的祖产,勉强能维持家中目前的生活。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么?你刚才难不成是借阿兄的钱买的首饰?”天水郡王佯作气恼之状,斜睨着他,“就算是我,一时间拿出数百金来也不容易。”他还是郡王呢,实封已有六百户,库房里也没有甚么东西。
“看来你以前买马斗鸡之类,费了不少钱财。”新安郡王挑起眉,“一匹西域宝马价值千金,听说打马球的时候便伤了好几匹?”若是宝马伤势太重养不过来,千金便算是白白耗费了。京城中众多纨绔子弟花钱如流水,根本不知经济庶务,又哪里知道千金在长安足以购置一座五进的大宅邸?
天水郡王一时喏喏不敢多言:“……那不是当初……当初不懂事么?”其实说来他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有自己的实封户,从来不会用越王府的钱财。不少狐朋狗友都是磨着家中的母亲与祖母要钱,转眼间便将千万钱撒出去。许多子孙繁盛的远支宗室多少都有些亏空,外头瞧着花团锦簇,其实府中早已渐渐支应不下去了。
“眼见着你便要成婚了,婚后总不能花用新妇的嫁妆。”新安郡王接道,“若是你爱马,咱们便试着开通西域商路,派人贩马。在西域买一匹宝马不过百金,到了长安便价值千金甚至数千金了。”
“当真?”天水郡王眼睛一亮,眼中尽是崇拜之意,“那咱们赶紧开个商路!阿爷常说我不懂经济庶务,又不肯费心思,日后必定会吃亏。我就知道,阿兄你一向懂得多!!只需紧紧跟着你,你让我做甚么就做甚么就对了!”
“子献?”李徽也不过是随口一提罢了。若论起经济庶务之事,他自然不如王子献,于是朝身边人看去。据他所知,王子献虽然将经济庶务之类的事都交给了孙榕与孙槿娘兄妹打理,却也绝非不通此道之辈,只是从未将心思放在这些上头罢了。
“西域商路?或可一试。”王子献含笑道。
当初宋先生带着他四处游历的时候,他的足迹不仅遍及了大唐疆域之内,且敏锐地发现了许多商机。孙榕与孙槿娘兄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悄无声息地便将东西南北的商路打通了。当然,若没有长宁公主的帖子,他们想成为纵贯大唐的豪商必定十分艰难。不过,经过这几年的经营,也总算是有些模样了。
打通西域商路当然不仅仅是为了钱财,更不是为了香料、宝马、宝石等贵重之物,也能顺理成章地搜寻西域沿途的消息,如灵州、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无论是永安郡王还是河间郡王,都远在数千里之外,消息稀少,急需探回更多消息确定他们是否怀有贰心。
越王府与濮王府的人都不方便行动,很容易让人寻着蛛丝马迹,牵连也颇深。但孙榕与孙槿娘兄妹这种“身家清白”的商人却是无碍——当然,长宁公主的帖子也不能一直用下去了。不过,生意若是做得大了,总该寻个固定的依仗才好。不然,无依无靠的富商不过是块人人垂涎的肉,只能任人宰割。
因着说起了西域商路,他们三人便又去了几家胡商铺子,看一看他们的香料、宝石、葡萄酒以及其他货物。直到西市要关闭的时候,他们才牵马离开。李璟策马回越王府,李徽与王子献则并辔前行,带着新买的葡萄酒,往延康坊藤园拜访宋先生。
二人到得藤园前时,守在阍室里的门子正与几位不速之客交谈。为首的少年郎大约与他们一般年纪,看上去很是稳重,不急不躁地辩解着,浑身上下都带着书卷气。而他身后则立着一个戴着白色幕篱的小娘子,轻纱之中,身形若隐若现。另有一名婢女与三四仆从背负着行李,散落左右,看起来都是练家子。
“此处难道不是王子献王状头所居之处么?某虽没有帖子,但对王状头慕名已久,烦劳入内通报一声。”那少年郎见门子看得紧,不由得一叹,从袖中拿出个沉甸甸的钱袋,“这些,便权作辛苦钱。”他虽看着像读书人,行事却颇有些商贾风范,实在很是灵活变通,且并不令人反感。
门子见状越发警惕,退后两步:“若是你为了见王郎君而来,又何必带上自家的小娘子?”并非他不通人情,而是那些榜下捉婿者曾使出无数手段想见王状头与宋先生。给钱财想进藤园的人每天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更有大胆的小娘子竟穿着丈夫衣,想跟着一群年轻文士们进来瞧瞧王状头。
就因着这些用尽手段抢新婿的人家,不单宋先生天天往慈恩寺去,连王郎君也被“逼得”另外赁了院子安置家人。这些濮王府出身的仆从见贵客如此无奈,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同情,自然更不会生出甚么异心,更勤勉地看紧门户,以免出现甚么“意外”。
少年郎顿时面露难色,门子便又道:“看你们风尘仆仆,应该是刚入长安,尚未住下来。不如先将家人安置妥当,再来求见王郎君也不迟。而且,实话实说,王郎君不堪扰动,已经搬离了藤园。如今在藤园中住着的,只有宋先生。”
“此言当真?”少年怔了怔,“王郎君究竟搬去了何处?”
门子摇了摇首,示意他并不能说。
于是,少年只能无奈地望向戴着幕篱的少女,甫要再言,便听少女低声道:“今日天色已晚,先住下来罢。明日一早,再过来拜会宋先生也不迟……宋先生应当知道……”她声音压得极低,几乎听不分明。
然而,王子献却眯起眼睛,翻身下马,细细端详那少女隐约的轮廓:“洛娘?”
少女几乎是惊喜地转过身,掀开幕篱,露出泪水涟涟的娇美脸庞:“大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