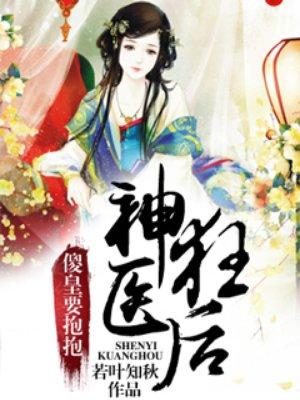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系列(共7册) > 第202章 男儿何不带吴钩(第1页)
第202章 男儿何不带吴钩(第1页)
据说1982年的元旦前后的那个冬天是我市百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气温直逼零下40度,我市西边那条大江的江面上冻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包。这个景象,山海关内的国人肯定是不曾见过,因为这即使在东北也不常见。
就在1982年的元旦那天下午,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匆匆地向火车站走去。
事后大家知道了,他之所以这么急,那是因为他要去打架,那把黑色的雨伞就是他那天后来横扫千军的武器。那时候并没有电影《黄飞鸿》,大家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曾有一位武学宗师一把铁伞横扫了广东。可是这人,为什么就这么有创意呢?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多年以后大家发现了,此人无论是穿着、打扮、坐骑乃至性生活都极具创造力。但此时,大家显然还没发现他有这天赋。
据知情人士说,他那天打着一把黑色钢骨伞去打架,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却穿着一条新的蓝色“的确良”裤子和一件新的军大衣。如果不打伞,那么这军大衣上的雪化了以后能在衣服上面结出冰碴子,这天寒地冻的,得冷死。而他只带伞没带武器的原因是那天他喝多了,忘了,忘带了。
他很酷,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没露出过一丝笑容,这可能是因为他天生就酷,可能是因为他喝多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被冻得面部表情僵化了。他身高约178cm,但体重却不到110斤,高挺鼻梁薄嘴唇,眉清目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小分头,油光铮亮。以当前的眼光看,此人绝对是个帅哥,充满了骨感美。要是他也像二狗一样写书,然后再染个黄头发,肯定超越郭敬明成为女粉丝追逐的对象。但他不会写书,只会开汽车、修汽车、打架。而且,以1982年中国人的正常审美取向来看,他也不算帅哥,因为那时候都是以胖为美,胖说明富裕、家庭条件好,就他这身材,一看就是五保户家庭里出来的。其实他并不是五保户,不但家庭条件挺好而且还是个复员军人,据说他当兵时表现还挺优异,但是自从复员以后就不怎么靠谱。
他复员以后当了我市东北郊某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但由于屡屡在街头打架被工厂除名,现在是纯粹的无业游民。有一个并不十分常用的词:“浑人”,这个词就形容他的。因为此人虽然心地还算是善良,但是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没少因为他的莽撞跟着他吃苦受罪,但他还一如既往的“浑”。通常人们心中莽汉的形象都是又粗又壮胡子拉碴的人,可这人的存在就充分地确定了这是个思想误区。因为他虽然瘦,但绝对是我市的第一莽汉。
他叫刘海柱,今天要赶往距离我市约30公里的段家屯。据说,那个屯子盛产惯偷,近期在市里经常盗窃自行车,当地派出所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和这群惯偷蛇鼠一窝,根本不管。
在半小时前,刘海柱在酒桌上听一个朋友说起了这件事儿。他的这个朋友在半个月前也丢了自行车,10天前去段家屯找到了那辆车把上刻着自己名字的永久自行车,找到的同时也遭遇了当地村民的毒打,车子没要回来,但门牙却掉了两个,现在一说话就嗖嗖地漏风。
刘海柱听说以后,看了看那个朋友四处漏风的牙,没多说一句话,穿起了新的军大衣,拿起了黑伞,径直走了出去。
“柱子哥,你去哪儿?”
“我去找点东西。”
说完,刘海柱就消失在了冬日下午的鹅毛大雪中。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冬日的下午,太阳只有盘子大小,挂在天上像是一个不怎么亮的黄车灯。
1982年的我市,是一个由灰色的楼、灰色的街道、穿着灰色衣服的人群和工厂烟囱里冒出的滚滚灰色烟雾构成的一个灰色的城市。当然,可能那个年代,全中国都是这个颜色。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刘海柱是这万灰丛中一点绿。通常情况下,刘海柱都是独往独来,绝对的独行大侠。他匆匆赶路是因为每天下午只有一班开往段家屯的火车,绿皮的火车。
刘海柱在那个灰色的火车站上了火车后一样很酷,因为这火车上没空调、没暖气,根本就不比外面暖和多少,那根本关不严的火车窗户呼呼地进风,刀子似地刺进火车上每个人的身上。他那已经冻得僵硬的面部肌肉一点儿都没融化,反而更加僵硬。那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流行了所谓的酷男,但在中国当时显然还没流行,刘海柱这样手里抓着把铁伞不苟言笑的男人显得卓尔不群,身边的乘客都在打量他。不过刘海柱一点儿都不介意,因为他的理念永远都是莫名其妙超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坐在刘海柱旁边的是系着粉色头巾子的一个大婶,正在和坐在对面的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看似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子聊今年庄稼的收成,坐在知识分子旁边的是一个系着绿色头巾子的小媳妇,不时地插话,三个人聊得热火朝天。刘海柱对他们聊的内容一点儿都不关心,他只惦记着朋友的那辆自行车。
但是东北人就爱唠,这三位又来找刘海柱唠嗑了。
粉头巾子大婶问刘海柱:“你家今年都种了啥?”
“我家是市里的,没地。”刘海柱本来想礼貌地笑笑,可是那冻得已经僵硬的脸笑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你在哪个单位上班?”黑框眼镜知识分子问刘海柱。
“……我没工作。”
“待业呢啊?你爸在哪工作?等你爸退休了你接班吧。”知识分子还挺为刘海柱着想。
“……”刘海柱没话说了。他都被开除了,还接什么班儿啊。
“城里人就是好,还能接班。对了,今年我家种了西瓜,夏天时用西瓜换小米……”绿头巾子小媳妇又开始说她家的地了。
刘海柱听见话题转移了,可算松了口气,他不敢再搭茬,又看似很酷的不说话了。其实他心里还是在打鼓,毕竟自己现在没工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段家屯离市里没多远,那火车虽然慢,但是很快也就该到了。刘海柱一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想到火车的连接处去照照自己的镜子,虽然是去打架,但是也要注意仪表。这也是古典大侠风范,就好像是子路跟人家终极PK时帽缨断了,他临死之前还说“君子死,冠不免”,最后戴正了帽子“结缨而死”。尽管刘海柱马上要面对的是一群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但他还是要整理一下妆容。
刘海柱认真地照了照镜子:嗯,还不错,瘦是瘦了点儿,但的的确确是个帅小伙儿。
反正已经走到这儿了,干脆下车前再上趟厕所吧,心情不错的刘海柱溜达了几步到了洗手间附近,伸手推开了洗手间的木头门……
只听见洗手间里面一声杀猪似的女人嘶吼:“谁呀!没看见我在上厕所!!!!”咣当一声,厕所门关上了。门关得太用力,重重地磕在了刘海柱的额头上。这一下关门关得实在太重,把刘海柱撞得天旋地转,一时间分不清东南西北,足足迷糊了两三秒。等刘海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时,他发现,几乎整个车厢人的眼光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冷了一下午的刘海柱这下暖和了,彻底暖和了,满脑袋都是汗,那没什么肉的脸臊得通红。他站在洗手间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手里居然还抓着洗手间的门把手。他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的确没有过这样的遭遇战。这就好像是学过高数的二狗解上小学的侄女的奥数题,二狗解了一晚上也解不出来,就算是看了答案都不会,真是丢人啊。现在,刘海柱也不会了。面对凶神恶煞的土流氓刘海柱知道咋整,但面对这一车人的眼光刘海柱反而不知道该咋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