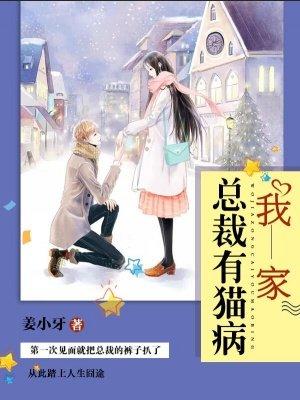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宫绣画和庄继华第一次是哪一章 > 第十七章 合书(第2页)
第十七章 合书(第2页)
“六个月了。”
“孩子出生便是冬日了,我尽力让皇上留吕大人到年后,只要姐姐顺利产子,到时候再格外为令尊求个情,怕是行得通。”
窗外秋烟静如横练,寒蛩秋蝉渐渐消退,萧合捡了一块鹅油松瓤卷递到吕毓书跟前,“姐姐跪了大半天了,想必肚子早饿了。”
吕毓书看着油津津的,心里又伤心,本来不想用,可是也知道萧合的意思是要她保重,念着孩子,便接过来,慢慢尝了一口,嘴里尝不出味道来,心里却是五味陈杂,一口,一口,一块,一块,含着泪吞咽了。
待到吕毓书起身回宫的时候,萧合才问道:“还有一事我实在想不通,万亭林的人如何就恰巧出现在北海呢?”萧合知道吕毓书不见得会知道,只是一问罢。
吕毓书却道:“皇后娘娘告诉我是孙度地,孙将军在北海。”
“皇后娘娘?”
吕毓书道:“皇后娘娘的父亲周大人,和我父亲向来交好。皇后娘娘近来身子不好,心里也难过帮不上忙,却将事情原原本本替我向周大人打听了。孙将军原先和万家相交甚好,皇上却相信他们。”她伤心,又累着了,说罢便去了。
七巧过来收桌上的点心,四样点心,却只下了半盘鹅油松瓤卷,不禁叹道:“又不是如奴婢家里这般艰难,好端端的,愉美人却要进宫遭这罪。”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萧合没有答话,只呆呆想着吕毓书一身杏花衣裳,这么多年,她依旧执着杏花。
正说着话,镜昭和小桂子也回来了,一路倒是多亏小桂子手脚伶俐,不曾被王礼发现,他果然是往元妃的凤音阁去了。
柳星因才到凤音阁,便见王礼从殿中出来,问道:“萧合那里又出什么事了么?”
“倒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循例来给元妃娘娘说些萧美人的日常罢了。”
柳星因知道他嘴里没有实话,给成儿递了颜色,成儿便从袖中取出一个荷包,拿出一锭银子来,正正经经的九八色纹银,王礼脸上顿时绽笑,又推了几回,方袖到袖中,道:“萧美人好似对吕府的事情很是上心。”
柳星因倒是不放在心上,眼下宫里没有人对吕府和吕毓书肚中的孩子不上心的,只“嗯”了一句,便往殿里去,却又停下来,叫王礼,道:“王公公在宫里多长时日了。”
“先帝九年的时候进宫的。”
“这么说,也熬了有三四年了。”柳星因又将一支玉搔头放在王礼手中,道:“以后凡是给元妃跟前禀告的事,也让我知道。以后还有的是好处,也不必三五年三五年的熬了。”柳星因见他面露难色,知道他害怕元妃,便道;“你不说,我不说,她不会知道的,多出的好处却都是自个的。”
柳星因本就气不打一处来,进了殿便将软玉的事情说与元妃,又道:“萧合的一个丫鬟都如此狂浪,不把娘娘您放在眼里。”
元妃自然明白柳星因的意思,只有一搭没一搭地擦拭着自己的紫玉笛,道:“呵,她可没来招惹我。”又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呢?我本想着这事与哥哥有牵连,不好亲自出面,可是本宫眼下掌管六宫,也不能不管,好歹她肚子里的可是皇室血脉,马虎不得。偏偏你得宠,皇上这一段时日只喜欢你,只好让你去皇上跟前替愉美人求情,你想必是气不过她比你早些有身孕,又去招惹她了吧。否则一个丫鬟是活腻了么,敢惹你这个皇上眼前的红人儿?”
柳星因听了这话,也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元妃又道:“你在这宫里再怎么着都好,我只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去招惹愉美人,你偏偏不听。”
柳星因道:“娘娘,您总是觉得愉美人性情淡漠又和气,你看看,她如今也知道到萧合得宠,跟着软玉去萧合宫里了,我觉着她平日里不过是铺眉苫眼,装模作样罢了。”
“难不成她不去求萧合,还去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