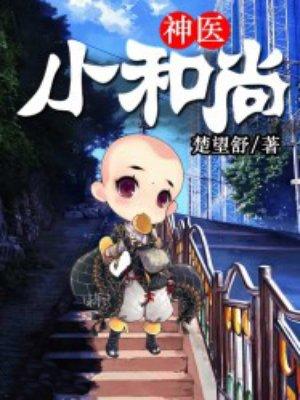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莫比乌斯环对戒寓意 > Chapter 59(第1页)
Chapter 59(第1页)
真是很久之前的一段故事,加上新过去的这一年,不多不少,已经整整走过去了十三年。
十三年前,她还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丫头,刚学外语没多久,背着她那十斤重的大书包,一边走一边背apple和banana。
她爸爸放了短假,白天在家做饭打扫,一日接送两回,到了傍晚放学时分,总是骑辆自行车早早地在门外等她。
她像个快乐的小乌龟,脑袋埋在书包下,坐在自行车的大杠上。每过一段小坑,他爸爸用阿语,声音高昂地说:小心屁股咯!
这一日下午却不一般,爸爸坐着辆大众桑塔纳而来,等她的时候倚在车门外,瞧见脑袋一点一点的苏童,挥挥手,说:“童童!”
爸爸帮她卸下书包,让她坐到后排座位,她一脸天真地问:“爸爸,你为什么坐上这车子了。”
爸爸没打算要立刻回答,前头开车的司机嘴快得很,说:“童童,你爸爸他啊,又要出差了。”
晚上爸爸带她去吃了一顿肯德基,点的儿童套餐里送了一个陀螺,上头有只身子老长的汤姆猫,一转起来,汤姆追着尾巴跑。
苏童吃不了两口就喊饱,一个人在桌下玩陀螺。
爸爸喊她她没应,直到妈妈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将她抱起来。
分别的时间来得这样早,她往妈妈肩头一趴,就开始流眼泪。
爸爸绕过来看她,按着她左右乱动的小脑袋,说:“童童,爸爸这次答应你,一定能早点回来。”
苏童满脸泪,抽抽搭搭问:“有多早。”
爸爸皱了皱眉,说:“很早。”
“你能答应爸爸好好念书吗?”
“我念书很好。”
“还有阿语呢?”
“我天天都在念。”
“会发弹音了吗?”
“……”
爸爸揉开她刘海,擦干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说:“下次回来,你念给爸爸听。”
他温柔地笑,一扬眉,一举手,发出一连串又响又漂亮的弹音,拖得又长,调子又高,像街口挥着扇子卖羊肉串的外地人。
苏童破涕而笑,拿手去捂爸爸的嘴,他哈哈笑着来捉,送到嘴边亲了又亲。
回到现实,马希尔问:“你爸爸也是个记者?”
苏童摇头,说:“不,他是个阿语翻译,阿语比我说得好多了,人又聪明耐劳。那时候国内兴起英语潮,能说好英语已然不易,更别提到今天都很冷门的阿语了。因为这个,爸爸是个香饽饽,但工作也局限,跟着国内的工程队来你们这儿合作搞基建,经常一出差就是大半年。小时候忘性大,刚刚熟悉了他就走,等他回来了陌生得很,说什么也不肯叫爸爸。”
马希尔说:“孩子都这样。”
苏童说:“就是那一次,他出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在这儿的工程队遇袭,好几个人都送了命。”
马希尔说:“你爸爸难道也……”
苏童说:“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只勉强找到几个人不完整的尸体,剩下的就都报成了失踪的,可能是被掳走了,可能是自己逃跑失散了,可能是那炸弹太厉害,把人炸得一点不剩了……可能性有那么多,但我爸爸是真的没了。”
自那之后,再也没有过消息,再也没回来过。就像大海中蒸腾出的千万水汽中的一小个,摆脱这束缚之后,便谁也不知飘向了哪一方。
明明理智告诉她,那种环境里,爸爸不可能坚持得了太久,但她心里的某一处还总是幻想着,他或许还活在这世界的某一处,可能残了,废了,失忆了,回不来了,但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人只要活着,有口气在,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