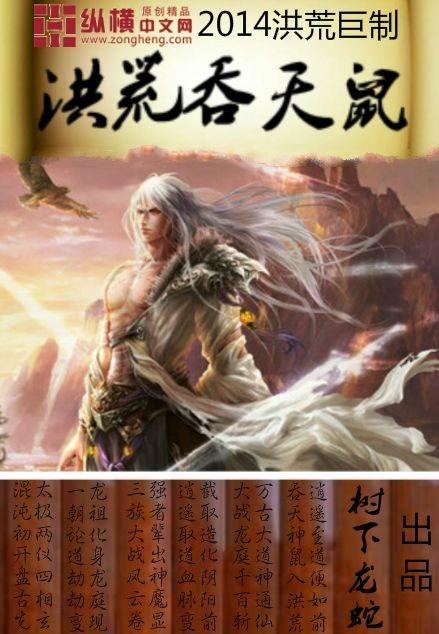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医妃权倾天下是虐文吗 > 第27章 霸道王女和她的小娇夫27(第1页)
第27章 霸道王女和她的小娇夫27(第1页)
琼林苑在燕京城外西侧,面南,与南池御苑相对,所谓的赐宴琼林说得正是朝廷于此处举办的新科进士宴会。
常言道人生四大乐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均不过小乐罢了,唯有金榜题名、打马御街最能令天下读书人心动。
三甲昭告天下后,摄政王按照天子惯例赐了琼林宴,虽是官家筵席,却少了礼乐繁复之苦,以娱乐为主。
伴随着钟鼓雅乐,一朝弹冠入仕的及第进士在席间酬唱和诗,好不热闹。
“探花郎在看什么呢?”说话是今科庶吉士卢琅舟,同时也是谢停云私交甚笃的同窗好友。
卢琅舟这边话音刚落下,正出神的谢停云赶忙垂下目光,含糊道:“琼林苑的栀子花开得好,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卢琅舟是个不胜酒力的,几杯下肚已有些犯了迷糊,自是未能发觉探花郎这番说辞的古怪,栀子花生在北侧庭院中,可谢停云明明看向的是西面。
可惜卢琅舟不疑有他,只揶揄道:“栀子花虽香,却比不上微之衣襟沾染的百花沁人心脾,探花郎打马游街的风采想是叫整个燕京都为你羞红了脸。”
谢停云这人脸皮薄,听完好友的揶揄,忽地双颊微微飞红,更衬得颜如渥丹。
琼林宴前,及第进士游街引得燕京城万人空巷,最挑眼的先是那位身穿鹤氅大红袍、脚跨金鞍红鬃马的状元娘子王嫣然,其次便是皎如玉树颜色好的探花郎谢停云。
历代探花皆为姿容佼佼者,而今科新点的这位探花郎更是容貌一绝。
若说燕京城的女郎们投给状元娘子的花果全因她们艳羡这位奇女子的文采斐然,那么掷向探花郎的鲜花香草则全是因为脸。
那红衣乌冠的探花生得极出尘,恍若谪仙入画,尽得那句“积玉阶前锦裳霞,眸转风流揽月明。”
世人皆好颜色,一时间,探花郎衣袍之上染尽燕京百花。
说回琼林宴上,见卢琅舟未继续追问上一个问题,谢停云暗自松了一口气,谦谦道:“少玄莫要打趣于我了。”
卢琅舟闻言哈哈一笑,又捡了些别的话打趣了起来。
只是他不知道,探花郎哪里是在看琼林的栀子花,尊位,坐西面东,那才是惹得谢停云出神的方向。
如今天子尚在宫中蹒跚学步,尊位之上,自然只能是代赴琼林宴的摄政王殿下,可对谢停云来说,那位剑履冕服的女子怎会仅只是摄政王呢。
当日上元一别,她便注定成为谢微之此生的不可说。
谢家二子谢停云,三岁识字七岁作赋,学于圣人言,习得君子艺,是生在谢家阶庭的芝兰玉树。他克己复礼,从来都是最端方不过的君子,却在上元灯节唐突了一位姑娘。
那日灯火阑珊,他望着气度斐然的女子走了神,直至看到人家在万千灯火下解开神鬼傩面,相赠于他。
见之难忘,那便不忘。
谢停云硬是以先立业后成家的为由推了家中说亲的打算,却辗转几年都未寻到其踪迹,本以为恩科之后再无可拖,却又峰回路转。
当日那个赤牙傩面的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大燕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于传胪大典上,手执金榜点他作今科探花。
谢停云原本是惊喜的,可却又莫名觉得委屈了起来,她看他的眼神并无半点波澜,仿佛从未见过一般冷漠。
到头来,竟只算是一寻常过客。
谢停云心绪茫茫,目光不经意间便落到了高台之上,他看得真切,摄政王眼中只有一个状元娘子,相谈甚欢。
“如今,扶摇胸中这口郁气可算尽消了?”顾七剑看向意气风发的王嫣然,笑问道。
从当初那个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闺阁女子走到如今,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王扶摇自是快意的,可这还远远不够,故而她脱口而出:“臣以为,还不算。”
“哦?说来听听。”
王嫣然接着道:“殿下所点的二十人,得入三甲不过五人,尚不到扶摇能志得意满的地步。”
世道苛责女子,单凭三人不过如旷野之星火,何谈重定乾坤,乾坤一日未定,她胸中这口对是世道的郁气就一日消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