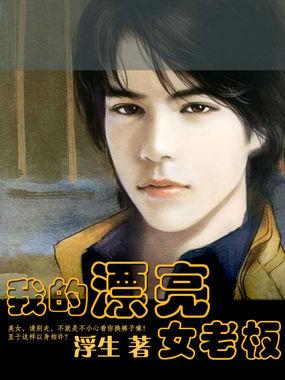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综花音少女男主是谁 > 151 第一五一章(第1页)
151 第一五一章(第1页)
“你喜欢这里吗?”
待在角落里尽量降低自己存在感的小小轰焦冻突然听到了自己身边传来的女声,这才发现有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已经清楚的认识到这群“人”神秘莫测的能力,所以轰焦冻在被吓了一跳后,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打量着这个之前并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女孩儿。
对方大概是国中生的年纪,穿着水蓝色的荷叶领半长宽袖及膝连衣裙,裸露在外的肌肤光滑洁白。她的头发是一种温暖的橘色,柔顺的打着自然的卷儿垂落至腰迹。大概是低头对自己说话的缘故,微微敛着眸的模样,让她看起来分外的沉静,甚至有几分冷郁的优雅。
不待轰焦冻回答“是否喜欢这里”这个问题,少女便移开了眼睛,用带着茫然与喜悦的神色注视着几乎可以称之为大型拆迁现场的群架场景,嘴角勾起了笑意:“真好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这么开心又自由的样子。他们平时被那些条条框框拘束着……或许这样会更好一点儿吧。”
轰焦冻突然难过了起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
美丽又健康的鸟儿将自己关进华丽的大笼子,乖乖的给自己关上笼门将自己锁在某处……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都是会难过的吧?
她那么真心的为这些人而感到开心,但是她自身却并没有她口中用羡艳的语气所说的“自由”吧?
这个少女,也是在被什么束缚着的——是某些很重要的人,所带来的约束与囚禁,似乎与他有着些许相似之处。
正因为如此,当少女伸出手问他“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出去玩”时,小小的男孩儿才会把自己的手掌放在对方的掌心中,任由对方将他拉出这个混乱的楼层,在没有惊动任何人——或者说像是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一样,悄然离开了这栋大楼。
大概这位少女也有着什么特殊的能力吧?她的步子很轻,却很稳。无论是手腕还是脚踝都那么纤细,却让轰焦冻感到了可靠与值得信赖。
“我叫齐木花音,你叫什么名字?”
大概是没有什么目的的闲逛,轰焦冻就这样被对方用右手牵着左手,漫步在行人并不多的街区上。
这条街上似乎更多的是公共机构与并不对外开放的博物馆等建筑,所以行人不算多,即使是在东京都,也算得上是相当安静的地区。
轰焦冻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某栋建筑的单向玻璃墙,深色的玻璃镜面上反射出的,是他怪异的红白中分发型和——没有任何疤痕的脸颊。
小男孩儿呆了一下,然后用右手去摸自己的左眼,果然感受不到烫伤后留下的狰狞痂痕。
各种事情都太过突然,他将手臂放在自己的面前细细打量,这才惊诧的发现自己的手臂上那些因为父亲的训练而留下的细碎伤痕也全都不见了!
“怎么了吗?”少女停下了步子,“手臂受伤了吗?”
“不,抱歉……”不清楚自己身上的变化的原因,又不可能对初次见面的少女完全吐露自己的秘密,小焦冻只是放下胳膊乖巧的摇了摇头,“我叫轰焦冻。”
“叫你焦冻可以吗?你也可以直接叫我花音。”确认了这孩子确实没在拆迁活动中受到伤害,少女便继续站直了身体,微微侧首低头,温声询问道。
“花音……”总觉得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发音,受到的精英教育让小朋友乍然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直呼其名并不太好,所以他迅速的补上了敬称,“姐姐。”
少女有些意外的打量的看了过来,仿佛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后她便笑了,像是在夏季静默盛绽的白玉兰,高贵而温润。
“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第一次有人这么认真的喊我姐姐呢。”
看着少女身上那份沉郁的气质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变得鲜活起来,轰焦冻来不及认清自己内心的满足感是怎么回事儿,便下意识的接上了话:“我在家里也是最小的。”
“那一定很受宠爱吧?”
只是顺应一般场景的闲话家常而已,本来有些开心的小孩子情绪再次低落了下去,含糊其辞:“……还好。”
“抱歉,似乎问了不该问的话。”少女仿佛有着一颗玲珑心思,瞬间就推断出了什么,然后诚恳的道歉着。
“不是的!你不需要……”对方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敏锐与小心翼翼和那毫无错处的礼节,让身为男孩子的小焦冻产生了烦躁的情绪——就算是被父亲当做透明人的、在这让人憎恶的“个性婚姻”中成为牺牲品的姐姐,看起来似乎也比面前这位少女要[自由]得多。
“嗯?”
小孩子再怎么有克制力也会遵循本能的希望去做事情。
轰焦冻不知道该怎么说,便模棱两可的说起了自己的情况来安慰对方——他就是觉得对方似乎很需要安慰的样子——所以说些什么都好,自己不应该如此抵触这个少女。
她就像是那种你一旦伸出手去轻轻一推,就会从此划开界限克制自身、即使再怎么喜欢也不会再接近的人一样。
想要……拉住她。
“我的父亲只是把母亲……不,把所有人都当成工具而已。”轰焦冻低声说道,“我只是他用来打败另一个人所制造出的工具罢了,所以……”
“诶?你是人造人吗?完全看不出来呢。”少女的思路瞬间拐到了小男孩儿完全无法理解的脑回路上去。
轰焦冻:……
“我有妈妈的!”小孩子炸了一下毛,而后又恢复了小酷哥的模样,低头踢了踢鞋子,“但是她……被父亲送走了。所以谈不上受宠不受宠什么的……我憎恨自己的父亲,却又依赖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