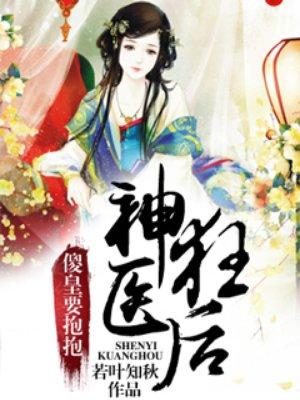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宇开霁百度 > 战鼓急声振地承蒙殿下厚爱(第1页)
战鼓急声振地承蒙殿下厚爱(第1页)
这天中午,镇国将军与华瑶议事完毕,竟然送了她两个侍卫——那是一对身强体壮的姐妹,出身于凉州北部,体格高大威猛,比戚归禾还要魁梧。
她们立在华瑶的身前,宛如一道人墙,结结实实地挡住了天光。
华瑶抬头望着她们“你们叫什么名字?”
镇国将军的一名亲信道“殿下不妨为她们赐名。十多年前,北部的部族被羯人灭族,将军收养了上百名孤儿。此姐妹二人根骨壮健,脱颖而出……”
华瑶很高兴地起了两个名字“那就叫紫苏和青黛吧。”
紫苏与青黛双双谢恩。
华瑶欢欢喜喜地把她们领了回去。
谢云潇作为军中副尉,手下也有好几百号人。他吃过午饭就去校场练兵了,没和他的两位兄长多说一句话。
如此一来,军帐里只剩下镇国将军以及他的长子戚归禾、次子戚应律。
戚应律的手里正捧着一只食盒。他埋头扒了两口饭,就听他的父亲问“应律,你打算在将军府吃几年的闲饭?”
戚应律抬起头来,对上父亲的审视“爹,我学不了武功。”
华瑶和谢云潇刚走不久,镇国将军便收敛了笑容。他不再是和蔼仁厚的慈父,眉目不怒而威,神色肃然冷厉,使人望而生畏。
他取下一把沉重的长戟,放置在案前,刀刃镀着一层暗纹,边沿凝着几点血迹。这把长戟杀过成百上千的羯人,历经重重血战,浸盛腾腾杀气,戚应律单看一眼,就头皮发麻。
“爹,”戚应律勉强挤出一个笑,“你不会想杀我吧?”
镇国将军淡淡地说“军营不止有武将,也有文官。你不会武,不妨来做文职。”
戚应律推脱道“爹,我懒散惯了。”
他爹说“你哥哥像你这般大时,领兵打胜了守城战。你姐姐远嫁康州之前,能一个人杀熊猎狼。你弟弟比你小四岁,刚在岱州剿完匪,从岱州运来的军粮再没少过半斤。”
戚应律笑着自嘲“诚如父亲所言,我是戚家唯一的孬种,比兄弟们差得多。您说,我何必来军营任职,讨您的嫌?眼不见为净。”
父亲怒声道“你懒散在家,赋闲多年,正事没做一桩,狐朋狗友交了一群。我谅你年少贪玩,也不曾严厉管束你。上月中旬,你去花街做狎客,远低过我的期望!”
他把长戟狠狠地摔在桌上“堂堂将军府公子!一事无成!一窍不通!竟学会了吃喝嫖赌!”
戚应律立刻跪下“父亲息怒。”
父亲袖摆一扬,竖立长戟,骂道“我息你个王八蛋!小兔崽子!高祖皇帝亲设的规矩,大梁兵将严禁滥嫖!你倒好,呼朋引伴去花街作孽!我戚家祖上几代忠烈,出了你这等纨绔!羯人羌人的六十万兵马蓄势待发,你还有心思吃喝嫖赌!你马上给老子滚去祠堂,跪满七天,对着列祖列宗叩拜请罪!”
戚应律垂着头,难以启齿,又不得不坦白“父亲,儿子真没嫖,只在花街瞧了歌舞。您若不信,传大夫来给儿子验验,仍是个雏儿。”
父亲却道“还有脸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有此逆子,不如无子!”
食盒被打翻了,汤水洒在地上,沾湿了戚应律的衣袖。他从小被父亲训斥,本该习以为常,但今天,他告密道“我在农庄住了四天,公主也在谢云潇的房里睡了四夜,您怎么不骂谢云潇沉迷美色?”
父亲皱起眉头。
戚归禾连忙为谢云潇求情“父亲,云潇向来谨守礼法,这里头兴许有什么误会,咱们都不晓得。或是云潇与公主情投意合,也算情理之中。他们二人年纪一般大,公主的性情活泼可爱,云潇……”
他尽力赞美弟弟的脾气“云潇沉稳冷静,断不会贸然行事。”
戚应律唯恐天下不乱“万一公主强迫他呢?”
戚归禾斥责道“二弟,你需得知道,云潇武功之高,远胜公主所有侍卫。我虽与公主交情尚浅,但看她大方爽直,断不屑于强迫他人。”
父亲终于发话“你二人替你们的弟弟瞒着此事,需得守口如瓶。”话中一顿,又说“归禾,你二十四岁,早该议亲了。你原先忙于军务,耽搁了不少事,爹也没替你相看……”
“爹!”戚归禾站起身来,直言不讳,“儿子有心上人了。”
父亲讶然地问他哪家姑娘,他不肯开口,只因他不晓得那姑娘对他是否有情。
旁人尊称他为镇国公府的长公子、凉州军营的明威将军,但他自认是一介粗鄙武夫,学不会花前月下的风情,也不懂琴瑟和鸣的美趣。他嘴笨舌拙,讲不出甜言蜜语,如何讨她的欢心?他经常惹她生气。
知子莫若父。父亲见他欲言又止,也没追问,只道“你既有此意,何不与她挑明?我戚家儿郎,行事光明磊落,不可畏畏缩缩。”
戚应律点头称是。
入冬以来,凉州下了几场大雪,将军府内的梅树次第绽放,红梅白梅交相辉映,满院梅香,沁人心脾。
华瑶却无暇欣赏雪景。她忙着接见凉州的勋贵,又要抽空与州府一同议事。每当她提起“剿灭三虎寨”一事,州府的官员都是喜忧参半,既有人支持她,也有人婉言相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