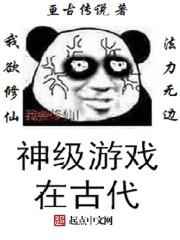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花与剑与法兰西推到章节 > 第一百四十八章 保证与奚落(第2页)
第一百四十八章 保证与奚落(第2页)
但是,虽然年轻,父亲多年的言传身教也让他性格变得谨慎至极。“万一陛下真的一意孤行,非要和我们作对呢?”
“如果他真要这么做,我会极端地反对他的决定,会尽我的一切能力来恳请他改变主意,一般来说,以他对我的信任,他确实会这么做的。”夏尔抬起头来,十分认真地看着理查德,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当然,凡是都有万一,如果一切真的无可挽回,帝国将会和奥地利交恶,而奥地利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我会挂冠而去以示抗议,退出帝国的朝廷,直到帝国改弦更张,重新走上法奥修好的道路上为止。”
“天哪!”
夏尔这个突如其来的承诺,让理查德惊讶得目瞪口呆,事实上他从没有期待过能够从夏尔的口中听到这样的承诺。“夏尔,你这是认真的吗?”
“十足认真,而且不是因为一时冲动。”夏尔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你可以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然后送到维也纳的外交部秘密存档,送给你的皇帝陛下,这是作数的,特雷维尔说话算话。”
“这……这还真是……”理查德视线四处游动,显然一时还没有接受这个消息。“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呢?”
“第一,我确实真心想要法奥亲善,容不得一点儿犹疑;第二,法奥修好是我一力倡导外交路线,是我所认定的法国外交基石,否定了这一点无异于是在说我的全部路线就是错误的,那么我必须引咎辞职,带着我的错误离开帝国政府。”夏尔仍旧显得从容不迫,仿佛是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事情一样,“第三,我有十足的自信,自己一定能够说服陛下和帝国政府,采纳我的建议。”
“是这样啊……”理查德急速地眨着眼睛,借此来掩饰自己的内心波动。
他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感受到十分强烈的自信,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是对的,也坚信他的陛下一定会按照他的建议去做。
这种自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他也不禁有些动摇了——毕竟,这个年轻人可是真的青云直上了啊,他确实有资格自信。
看来,这个试探,是相当圆满了,理查德心想。
“很好,夏尔,我会把你的话和你的承诺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陛下的,我希望这个承诺不用到需要兑现的那天。”他站起来,然后郑重其事地走到夏尔的面前,“另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奥地利人对法国绝无恶意,只要法国人向奥地利人伸出友谊之手,那么它绝对不会落空。跟你一样,我也用我的前途来保证,如果法国无过错而奥地利主动和法国决裂的话,那么我愿意挂冠而去,回家摆弄我的花园去。”
“你这么一说,我倒深怕我们某天要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麓之下种花了。”夏尔突然笑了出来,然后自己也站起来了。
“那自然是不会发生的啊!”理查德哈哈大笑。“不过,如果您想去的话,那么奥地利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
因为心情都很好,两个人又握起了手。
从理查德的面孔上,夏尔判断今天自己已经超额满足了对方,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复,并且明确了奥地利的立场,而经过两个人一番畅谈之后,时间已经来到深夜时分了。
正当夏尔以为对方就要告辞离开的时候,理查德突然又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夏尔,您还记得那位俾斯麦先生吧?”
“嗯,我还记得啊,我和这位先生曾经一起受您父亲的邀请拜访过他的庄园。”夏尔马上点了点头,“我还和他交流过几次,我认为他是个聪明人,而且很积极。”
“您看得很不错,他确实是一个聪明而且积极的人,而且是过于的聪明和积极了。”理查德的笑容更加深了,似乎有些嘲讽似的。
“这是指什么呢?”夏尔马上问。
虽然他心里很注意,但是他表面上却装作不太在意。
此时的俾斯麦,只是被普鲁士国王扔到了法兰克福当驻帝国会议代表而已,虽然身份挺高,但是基本上等于被投闲置散,无法参与机要,所以只是一个闲杂人等而已,和他这样的帝国大臣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他要是表现得过于关心那才是奇怪。
“这位先生,现在一直都利用各种场合,刺探法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似乎是想要弄清楚弥漫在欧洲上空的阴云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还和俄国人驻法兰克福的代表过从甚密,依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似乎一直都在提出各种建议,想要俄国改善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以便缓解外交紧张。”
“这倒是并不太令人意外。”夏尔想了一下之后,低声回答,“虽然和他见面不多,但是我看得出来俾斯麦先生不是一个喜欢安分的人,况且普鲁士人一直都对俄国很有好感——不过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特别执着于亲俄的人。”
“他当然不是特别亲俄的人,普鲁士人除了自己谁也不亲。”说到普鲁士的时候,理查德的态度就没那么好了,显得特别尖刻,“普鲁士人一直都这样,他们就喜欢耍弄这种鬼把戏,抬高自己的地位,而这位先生更有这种需求,因为他觉得帝国会议代表太屈尊他了!他想要多做点儿事,多扮演点角色,尤其是扮演西欧和东欧的仲裁者角色。”
“您的意思是,俾斯麦先生并不关注俄国和西欧的外交关系能否缓解,他只需要借助这种紧张空气,来抬高自己的地位,顺便为自己增加影响力,以便在未来为自己谋取一个……更有利的职位?”夏尔平静地问。
“是啊,普鲁士人喜欢冒充大国,这位先生喜欢冒充大人物,所以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刻,他上蹿下跳想要扮演一个他配不上的角色,是很正常的。”理查德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刻薄地嘲弄了俾斯麦一番,“但是,在欧洲的至高舞台上,普鲁士人只能是看客,而被扔到了法兰克福的他,充其量只能算是看客的看客,他的全部努力就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一场滑稽剧而已。”
他这么尖刻,既有奥地利人对普鲁士的传统厌恶,也是想要在夏尔面前败坏俾斯麦的形象,以免夏尔对这个普鲁士人印象过佳,印象他对奥地利的亲善态度。
“如果他愿意演的话,那就让他演吧。”夏尔又想了一下,“就算他想要玩弄外交阴谋,反正无关大局。或者说,这还更加是好事……越是让俄国人以为自己形势还不算很严峻,他们越就会得意忘形。”
“那么您介意不介意让他吃点儿教训呢?”理查德突然问,“比如我们在和普鲁士谈判的时候,对普鲁士国王抗议他的行径?”
“现在还是不要这么做吧。”沉默了片刻之后夏尔回答,“这个人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