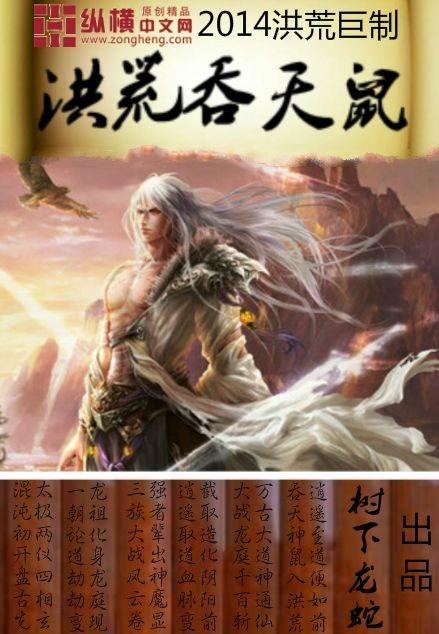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光阴童话艾小图 天地23 > 第17页(第1页)
第17页(第1页)
季时禹本来是逗池怀音玩儿的,没想到她会突然这么说,他嘴角抽了抽,最后指了指自己的脸,不悦地问:“我像小白脸?”池怀音被他严肃的样子怔住了,想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回答:“……好像确实不黑……”季时禹冷哼一声,低头瞥向池怀音。池怀音原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双手一伸,挺无赖地说:“我们都没票了,你说到做到!”……那之后的几天,池怀音都十分拮据。究其原因,就是季时禹太黑了,池怀音本来是要把吃不完的饭菜票给他,结果他跟抢劫的一样,全拿走了。等她后悔懊恼的时候,季时禹那个小流氓,已经拿着她的饭菜票挥霍去了。哎,人果然还是不能太好心。池怀音本科四年,都没有找过池院长使用任何特权,这次心理建设了许久,才终于向院长开口求助。池院长带她去职工食堂吃饭,周围都是院里的教授、老师,来往都会和池院长打招呼。对这样的阵仗,其实池怀音并不是很适应,他们在学校里一贯接触很少。“这个月是不是吃太奢侈了,饭菜票居然都用完了?”池怀音低头吃着米饭,低声回答:“请同学吃了几次。”对此,池院长倒是没有责怪:“和同学还是要打好关系。”池院长抬头打量了自家女儿一眼,见她手腕空空,疑惑地问道:“我从德国给你带回来的手表呢?怎么不见你戴了?”池怀音听到父亲提到手表,心理咯噔一跳,随后摸了摸自己的手腕道:“放寝室了,做实验不方便。”池院长对此倒也没有怀疑,从包里拿了些饭票菜票给了池怀音:“给学生的我不能给你搞特权多发,这是我的,你这几天就在职工食堂里吃。”“好。”气氛有些微尴尬,池父叹了口气,顿了顿声:“要是有合适的男孩子,也可以处处看,免得你妈老说我用学术害你。”“嗯。”想到池怀音班上那些人,池父又有些不放心:“不过也不是什么男孩子都要接触,你们班那个季什么的,那种小痞子,还是少接触。”想到某人之前对池院长做的事,她真的忍耐力极好,才能不笑出来,清了清嗓子,还是一贯的乖巧:“知道了。”……季时禹其实也很少穷成这样,他家里干个体户干得早,等个体户开始普及推广的时候,季家的杂货铺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扩建加盖,初具一个小超市的规模。在大城市可能不值得一提,在小城市倒算是家境殷实。要不是赵一洋,他不至于沦落到黑池怀音的饭菜票。赵一洋知道季时禹拿了池怀音的饭菜票,一边抨击季时禹不要脸,一边跟着季时禹蹭吃蹭喝,真的没有底线。“我怎么觉得池怀音那姑娘,好像看上你了?”赵一洋吃饱喝足,坐在椅子上剔牙:“怎么你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季时禹皱眉,对赵一洋的说法十分不齿:“她好像很怕我,每次见到我都恨不得要发抖,估计怕我找她麻烦吧。”“这说起来你也有错啊,人家一个乖乖女好姑娘,你老为难人家干嘛?”季时禹乜了他一眼:“要不是你要追她室友,我和她本来并没有什么交集,谢谢。”一说到心上人江甜,赵一洋无赖的脸孔又出现了。“那你还是要继续,让池怀音怕你,这样我们下手更方便。”“滚——”……艰难的一个月终于过去,学校发了新的饭票和菜票,每人定量。这一天,食堂的人都比往常多了。下午阳光明媚,同学们已经早早在实验室就位。池怀音作为班上唯一的女生,开学就在担任生活委员,从老师那拿了这个月寄来的信和汇款单,最后一个到了实验室。将各个同学的信和汇款单分发到位,最后到了季时禹和赵一洋身边。“你们的。”说着,将汇款单递上。赵一洋拿到汇款单,第一反应就是恨不得飞出实验室去拿钱,要知道他月底超支,已经靠找别的同学东借西借度日很久,兜里就剩三块钱。比之赵一洋的雀跃,季时禹倒是很淡定。拿到了汇款单,随手揣进口袋里,季时禹的视线又落回桌上的实验材料上。池怀音站在他身边,略微有些紧张地咬了咬嘴唇。本以为他会和她说几句话,结果他那么专注做着自己的事情,这让她不由有些失落。“那我走了。”她轻声说。“嗯。”季时禹头也没抬,黑而浓密的头发盖住了他的表情。那之后,除了上课做实验,池怀音几乎看不到季时禹那帮子人。据说男生拿了生活费,都会荒唐一阵,也难怪一到月底就一个赛一个的穷。真奇怪,以前走在路上看见季时禹,都恨不得扭头要跑,如今偶遇不上,竟然还觉得有些遗憾。这种柔肠百结的感觉,池怀音十分陌生,也非常不习惯。晚上江甜有晚课,别的室友也要去图书馆。池怀音晚饭就随便对付了一下。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她不想胡思乱想,打算早些睡。结果刚一躺下,寝室的门就突然被敲响了。池怀音爬起来开门一看,竟然是个完全不认识的女孩。“你是304的池怀音吗?”“我是。”池怀音有些莫名:“你是?”“楼下有个人叫你下去。”池怀音有些诧异:“谁啊?”“不认识。”那女孩说:“他就让我帮忙叫一下304的池怀音。”说完又低声道:“长得怪好看的一男的。”……池怀音披了件外套下楼。还没走出宿舍,就看见不远处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想了几天,本想让自己冷静,却不想又冷静不了了。银白的月光淡淡地,通过枝叶罅隙照下来,斑驳光影,都落在他身上。夜风微凉,撩起他额前的碎发,露出他有神的眼眉,就那么看着她的方向,害她忍不住紧张起来,恨不得走路都要同手同脚。池怀音感觉到心脏好像失序的琴键,开始乱弹一通。“季时禹?你……你找我?”季时禹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的老榕树下面,那画面,看着一点都不真实。他看了池怀音一眼,微微挑眉,将一个冰冰凉的东西粗鲁丢到她身上。池怀音险险接住,低头再一看,那块停走的梅花手表,赫然重新出现。手表抵给情人岛那个民宿老板娘了,上次池父问到的时候,池怀音原本打算去赎回来的,可是情人岛还是远,她一直没机会去。没想到……怪不得季时禹今天都没有去实验室。其实这块表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即便它比较贵,但对池怀音来说,那不过是身外之物,要不是怕池父念叨,她根本不想去赎。此刻,风吹得树影沙沙,季时禹就那么站在她面前,月光洒下,他的影子有一半落在她身上,好奇怪,明明没有接触,却有一种很亲昵的错觉。他的表情坦荡得狠,表情依旧痞痞的。“上个月的饭菜票,谢了。”他转身离开,临走嘱咐她道:“以后不要随便拿表抵押,现在这块表增值了,值七百了。”夜灯朦胧,将那人的背影描摹得格外幽邃。池怀音凝视着他离开的方向,甚至忘记了呼吸。他刚拿了生活费,居然花了一百块钱去赎她的手表?值得吗?那一瞬间,那种酥麻的悸动,像春天的花骨朵,忽而一夜绽放,在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作者有话要说:某人:我看到一种说法,男人不该让女人流眼泪。池怀音:废话。某人:因为女人的眼泪都是脑子里进的水,如果流干了,男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