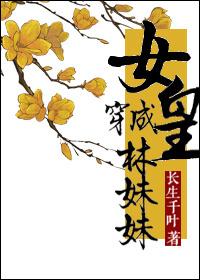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乌云遇皎月第一次哪章 > 第74章 谭皎十3(第1页)
第74章 谭皎十3(第1页)
和壮鱼分手后,我开车在街上闲逛。想到她说的“不对劲的地方”,心里还有点发毛。
对于我这样一个宅女来说,这还真是个有难度的问题。除了偶尔旅行,我基本都是家、图书馆和餐厅三点一线生活着。
难道,是在我失去记忆的那一年里,去了什么了不得的地方?而我不知道。
不。
我心中涌起一个清晰有力的念头——就是那条船。
佐证就是我的记忆、邬遇的双眼和言远操纵群鸟的神奇能力。如果那股神奇的宇宙力量真的存在,都能弯折时间线了,那能造成这些古怪的影响,也不奇怪了。
没有比那次旅行,更不对劲的了。
后来船上的那几天,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又遇见了什么?
下意识我想到,得赶快把壮鱼的推论告诉邬遇。然后我一颗原本紧张的心,立刻像被戳破的气球,蔫了。有什么可告诉的?他已经走了,不回头了。我还跟他商量个屁宇宙大事。
我闷闷地把车往回开,不知不觉,竟又开到汽修店外。我把车停在马路边,静静望着。曾几何时,在意过这里?现在居然连看到门口扔着的几块轮胎皮,都有种微痛的亲切感。
他已经走了,十多天前,他们说他辞职了,不在了。
而我,是真的失恋了。
我把车开到店门口。一个脸生的伙计迎上来说:“美女,有什么事?”
我说:“洗车。”
他说:“哦,本店刚开业,要不要办卡?”跟我第一回来的说辞,一模一样。我笑了笑,说:“不用,我办得有卡。”可在钱包和车里找了一阵,那卡却死活找不到了。
伙计有点为难:“小姐,我们的卡是不记名的,这卡没带……”
我有点心烦,说:“行了,我给钱,洗吧。”
他们开始洗车,我站在店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看着远方,晚霞映照下的城市,格外温柔宁静。我的心也平静不少,踩着我难得穿的细高跟鞋,沿着窄窄的马路边缘,手背在背后,一步步地走。
“遇哥。”隐隐约约,店里有人喊了一声。
我的耳朵就像被人刺了一下。我停下脚步,也许是,听错了。
我抬起头。
风吹得整个天空都呼呼作响,晚霞张牙舞爪的蓝天之下,一个男人站在店门口。穿着我熟悉的白背心,牛仔裤。指间有支烟。隔得远,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依稀辨认出头发更短了些,脖子上闪着汗珠。
他也看着我的方向。
他的眼睛6。0,此刻连我脸上的毛孔都能看清楚。
我身子一歪,从马路边缘踩下来,姿态绝对又傻又狼狈。可这么安静的时刻,我的心却像是被沉进了一坛子苦酒里,又湿又重又涩,还找不到出口。
我慢慢地再次抬头,却看见他已和小华、另外一个伙计,从店门口走出来,朝我的方向走来。小华说:“遇哥,你终于回来了!必须去吃一顿给你接风啊!”另一个人说:“是啊,遇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邬遇的声音很低,我没听清楚他答了什么。
他们从马路对面走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小华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我,却没有打招呼,只打量了我几眼,跟着邬遇走了。
邬遇他没有看我。他是不是觉得我想要纠缠不休,所以根本不看我。
他不看我。
车洗好后,我开了一阵子,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乱转。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是他刚才的样子,低着头,眉目清冷,就像十多天前那个吻,只是我的错觉。
我想,很好,他看起来已经很平静,根本不受任何困扰。男人果然比女人果断狠心多了。
我也要平静下来。那事就不要再想了。
我不要了。以后我也不会再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