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页小说站>似曾相识兔归来 > 第53章(第2页)
第53章(第2页)
九念一听便心急的站了起来,走到军帐门口,却被两把军刀挡住了去路。
她留在这里本就是王孝杰网开一面,看在姒华言的面子,而这两个兵卒是绝不会允许她离开营帐半步的。
正焦急之际,姒华言正从不远处走来,看到九念站在门口望着自己,便挥了挥手,两个兵卒放下了刀。
姒华言一眼掠过她面容里的焦急之色,便知道她的为了什么,用身子挡在她面前,负着手,语气平淡的问:
“你又要赶去救人?这一次,又要断哪一根手指?”
九念一句话也不多说,只是坚定的看着他,冷冷的说:“放我出去!”
姒华言墨黑的眉眼之中有些倦意,却还是打起精神来劝告她:“你以为你是谁?能够救得了所有人吗?”
九念抬了抬下巴,眸中升起一道透明的、疏离的城墙:“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的事,我曾九念做不到。”
她是在怨他。
姒华言的眼波动了动,正要说些什么,她便越过他的身子走出了大帐。
姒华言拗不过她,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九念和姒华言赶到了军营的马厩处,王孝杰正在怒不可遏的对着两个兽医训话,一群马倌小兵都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作声,其中便有二师兄一个。原来战马生病的消息传到王孝杰那里,有人举报说马倌、兽医玩忽职守,对战马照顾不周,致二十多匹马生病,而他们竟在军中玩起了骰子,带头赌博的正是新来的小兵清无。
眼看着军中战马有可能得了瘟疫,迎来灭顶之灾,战事不顺的王孝杰大发雷霆,焦躁万分。
九念正是在他气头上赶到的,本想去求情,可还没等九念说话,姒华言便侧头拦住了她,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去马厩里看看,到底是不是瘟疫。”
他往日便知道九念自小最擅长与马打交道,这是在给她指出路。
姒华言说完,便上前一步,与王孝杰交谈,九念趁机进入了马厩,在这些瘫软在地的战马中摸摸拍拍。
这些马有的正在拉肚子,透明的臭水从马屁股里排出来,发出粪便的气味,九念丝毫不嫌弃,低头在地上闻了闻,然后又翻看了每匹马的眼睛,皆有流泪之状。
她站起来,望着这些瘫软的马儿,陷入了思考。
以前,冀州驿的驿马也出现过此类症状。
王孝杰那边,正急得横眉立目,对那兽医说道:“竟敢在军营中行赌?玩忽职守,害我的战马得了马瘟,简直罪不可恕!来人呐!军法处置!”
两个小兵走过来,架住其中一个年轻的兽医,手起刀落,便将他的人头砍了下来!
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纷纷磕头求饶!
王孝杰又问另一个吓得尿裤子的兽医说:“本将军就给你个赎罪的机会,明日之前若是治不好本将军的战马,你,还有你这个光头!你们这些喂马的也得军法处置!”
二师兄哆哆嗦嗦的,帽子都掉了,光头上一冒汗,显得更亮了些。
王将军回头,不经意间瞥见了九念,冷冷的哼了一声!
王孝杰走后,姒华言走到九念身边,看着她问道:“看出什么了没有?”
九念还是不肯正眼看他,只是回头蹲在地上,摸了摸其中一头战马,道:“不是瘟疫。”
姒华言挑了挑眉:“能救吗?”
九念站起来,远远的叫了一声还跪在地上的清无,道:“二师兄!你过来!”
清无已经两天没见到她,此时见她穿了一身青布衣裳,这布衣有些像庶人男子的款式,她短短的头发,仍旧是锋利如男子的眉眼,受伤的手上还缠着布。便赶紧跑过来,握住了九念的手,担心的问:“小师弟,这指头没断吧?啊?给二师兄看看。”
二师兄鲜少露出这般正经的神色,只因实在感激九念的救命之恩,此刻拿起九念的手,心疼的摸来摸去。
姒华言轻咳一声,将目光扭向别处。
九念笑了笑,又忽然转了一副责备的面孔:“你瞧你刚才吓得,出息,我平日说你什么来着?不让你赌不让你赌,你偏不信!这下捅了大篓子了吧?”
二师兄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从地上捡起帽子戴上,忧愁的说:“这下完了,我死定了!”
九念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走到那几个跪着的小兵面前,说道:“你们几个,想活命的话,现在就去帮我找二十根干竹条来,再生上火。”
那些人知道见九念如此气场,身后又粘着姒华言,便赶紧去找竹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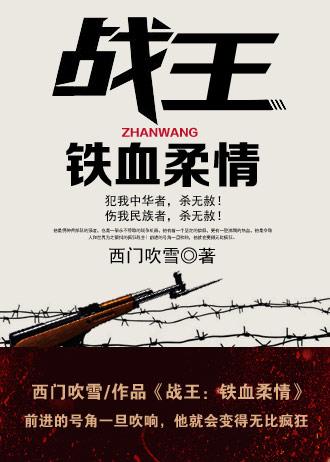
![真男人不搞假gay[星际]](/img/13693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