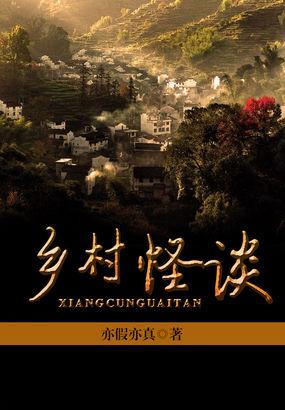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小药妻txt宝书网 > 第142章 小药妻淡樱(第3页)
第142章 小药妻淡樱(第3页)
阿殷叹道:“还是老样子,不过仔细想想,她气急败坏也是有道理的。她母亲生前一直被永盛帝折磨,她想要借你的手报仇也是情理之中。只是如今永盛帝已驾崩,她再恨也不该总想着让我们撬新帝的皇位。”
“她只是没想通而已。”
阿殷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遗诏是假的?好让她死心。”
沈长堂摩挲着她的手,只觉整个上午的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不必说,她当初欺负过你。”阿殷哭笑不得:“多少年前的事了,我都不记得了。”
他道:“我捧在掌心里的人,自己都舍不得欺负,一想到别人欺负过,我心里难受。”
他这么一本正经地说,让阿殷嗔了他好几眼。
“说得好像当初你没欺负过我一样似的。”
手掌不老实地下滑,阿殷拍了拍,说:“别闹了,这里还是御书房,我明早还要去绥州呢。”
感觉到身后的人变得僵硬,阿殷侧过头,说:“我前天晚上和你说过的。”
“有吗?”
阿殷睁大眼,说道:“有!你还和我说早去早回,上官东家醒过来了,我有事儿要请教他。”
“有吗?”
阿殷说:“当时你还让我的腿抬高一点!”话一出,阿殷反应过来,张嘴在他手掌上狠狠地就咬了口,说:“你再耍流氓,今晚你就睡书房!”
沈长堂道:“娘子,我错了,我记得,记得了。”说着,他又道:“皇帝再过一年便十五了,礼部那边开始选秀了,有许多好姑娘。你那知音不是还没娶妻吗?我挑几幅画,你去绥州的时候给他送去,问问有没有看得上眼的。”
阿殷说:“醋坛子侯爷!”
沈长堂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理直气壮地摸着阿殷的肚子,说:“待会让御医过来给你把脉,要是有了未来一年你哪儿都不能去,好好养胎。”
阿殷听到这话,神色不由柔和下来。
“好。”
她也想要孩子,比任何人都想。
当夜,醋坛子侯爷非常卖力,以至于次日阿殷启程去绥州的时候,是坐着轿子上马车的。
。
到绥州后,已是一个多月后的事情。
阿殷要回来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上官家,林荷格外开心,抱着咿呀咿呀学语的小男娃和阿殷说了许多话,直到元贝受不了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夫妻俩拌着嘴,阿殷含笑送两人离开。
“他们每天都要拌嘴。”上官仕信走进来,温声说:“但一入了夜,两人又甜得方圆百里之内连蜂虫都不敢靠近,太甜了,怕黏着。”
阿殷被逗笑:“小夫妻感情好。”
上官仕信道:“我父亲在屋里等你。”阿殷点点头,跟着上官仕信往仁心院走去。一路上,上官仕信与她说以前的见闻,两人极有默契,虽将近一年未见,但不见丝毫陌生。到了仁心院后,阿殷见到了上官仁。上官仁恢复得极好,比起以前虽消瘦了不少,但已经与以前差不多了。
上官仁见到她,便道:“果真是缘分,是我眼拙,我早该认出你。这世间除了元公的孙女外,还有谁能得他真传?”
阿殷道:“东家可见过我祖父?”
上官仁道:“小时候见过几面,你祖父真的是天生就吃核雕这碗饭的人。只可惜……”他叹道:“倒也不瞒你,上官家之所以飞来横祸,是我好奇心太重,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才惹来了皇帝的杀心。”
“不该知道?”
“上一代的真相。”上官仁道:“太|祖皇帝曾救过一位南疆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份藏宝图。”
阿殷道:“江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