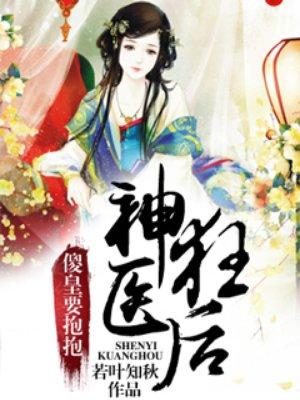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重生大周陆羽 > 第一百四十章 行刺皇夫(第1页)
第一百四十章 行刺皇夫(第1页)
)
这夜的紫阳城雾气笼罩。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任凭浓重的雾气将城内的街道和城外的旷野覆盖。再加上时值夜半,暮色深重、月色不明,能见度真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这一场跟秋天的干爽天气格格不入的大雾,不由得让人感到充满了诡异的气息。左瑛坐在赶往城门的马车上,放下轻轻挑起的窗帘,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真相是怎么样的,又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假设这个徐弘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潜伏在紫阳城,一再要求参加城防,又杀害提供情报的人灭口,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只能指向一个动机,那就是要破坏紫阳城的防御,帮助敌军攻城。
如今对于敌军来说,攻破紫阳城最大的障碍,不是城墙坚不可摧,不是紫阳城兵精粮广,也不是她左瑛坐镇在此,而是有阿史那无期这个不光作战经验丰富还能以一当百的猛将作为统率。
跟城外敌军里应外合的最佳手段只有两个:一个是骗开城门放贼兵进来;另外一个,显然就是除掉阿史那无期。紫阳城律令森严,早有规定下达,如非亲见女皇或者皇夫,无论得到任何其他人的命令都绝对不可打开城门。不光不能开门,还要立刻将传令的人捉住,送去给女皇和皇夫亲自审问。
所以,要跟敌军里应外合的奸细可能做的事情只剩下一件。
现在这个时候,即便打着火把,街道上的能见度也不超过五米。但是仗着最近实行宵禁,路上应该没有人,御人在左瑛的催促下一路策马疾行,两刻钟后终于赶到了与敌军对峙的西城门楼下。
城下戍卫的士兵看不清来的是何许人,只是从火光和声音上判断有车马逼近,所以早就振起长枪,喝问着来者何人。直到看清楚了来的是左瑛和绯羽,才纷纷下跪行礼。
“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徐弘?”左瑛一边问,一边不停步地往通往城头的阶梯上走。
“有,就刚刚上去没多久,说有重要的军情要跟皇夫殿下禀告。”一个士卒回答道。
左瑛心中一惊,果不其然,“皇夫现在哪里?”
“回陛下,应该还在城头巡逻。”
左瑛提起裙摆,三步并作两步地快速攀爬着楼梯。绯羽提剑紧跟在后。
左瑛心想,阿史那无期胸坦荡、没有城府,即便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也只会当面嗤之以鼻,而不会提防着有人会在暗地谋害他。就算跟他直说有人要害他,只要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无怨无仇,他也不一定相信,更何况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小心警惕一个本来就跟他们一路同行的人?他不可能做得到。想到这一点,左瑛心中更加急切,一个不小心走神,险些被脚下那些又高又陡的阶梯绊倒。
城头上两边城墙每隔五米就安插着一个点燃的火把,稍微能够驱散一点城头的雾气,让在上面戍卫的士卒至少能够看得见十几米外的对面有人没人。
城头的一角,阿史那无期带领的巡逻队伍已经解散。只剩下两个人立在墙边。
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红色战袍的那人正是阿史那无期,而另一个跟阿史那无期相比之下略显柔弱清瘦的则是徐弘。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快说,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磨叽。”阿史那无期有点不耐烦。但是左瑛告诫过他不要动不动就对看不顺眼的人发脾气,所以他自觉收敛了一点,在徐弘来见他说有重要事情要单独禀告的时候,他还是让已经结束巡逻的士兵先行散去,自己留下来耐着性子听他禀告。
“皇夫,”看见左右无人,徐弘上前一步,略带点激动道:“徐弘对不起你!”
阿史那无期奇怪地皱起眉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徐弘“噗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地,露出愁苦的神情道:“皇夫,徐弘心中一直有个郁结。身上的伤虽然好了,但是心中的结却打不开。”
“喂,你跪什么跪?”阿史那无期不是觉得自己受不起,而是觉得一个老爷们没事哭丧着脸跪在你面前,真有点肉麻想吐。
徐弘将头垂下,用带着哭腔的声音道:“皇夫,其实那次带兵去平州城遇袭的事,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没有说出全部的实情……”
“那实情是什么?”阿史那无期已经被这个开头吸引住了,他想知道徐弘到底藏起来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方的声音有点小,周围能见度又低,他不自觉的往前挪了一步,弯下点腰来看着徐弘。
徐弘跪在地上,低着头,垂着双手,沉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