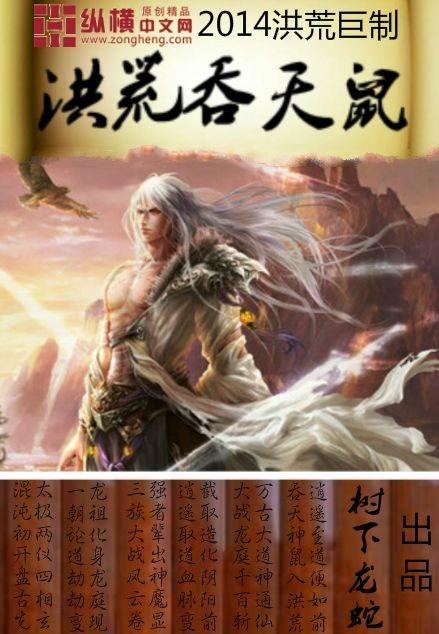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hp之异乡上 > 63ACT485(第1页)
63ACT485(第1页)
流萤在浓厚的夜色下漫无目的兜转,细如发丝的光晕在它们身后划着弧线交织,在挺拔的枝干间若隐若现。广茂繁硕的叶影层层叠叠,晚风吹拂着摇摆出沙沙的乐音,层叠处掀开宽窄不一的缝隙,可窥见少许满天繁星。稍纵即逝。缝隙重又闭合,却不再像最初那样浓密,渗透出丝丝缕缕的光和斑斑驳驳的青。
深沉的夜并非墨黑,而是一种仿佛含着光的蓄势待发的藏青,只等着破晓的晨曦划破苍穹,吐故纳新。
海姆达尔突然发现自己多愁善感了,三更半夜形单影只的立在林边陶然了。在他的概念里只有诗人或者艺术家才会这样,用挥霍生命来诠释感性。
斯图鲁松室长不认为自己是个有情调的感性之人,曾尝试让他学会欣赏艺术的克鲁姆夫人指着他的鼻子斥他“俗不可耐”,海姆达尔不反对这个说法。克鲁姆夫人的娘家家境殷实,嫁人了之后衣食无忧,人的品味在一定程度上由经济基础决定。即使如今的海姆达尔同样衣食无忧,但他从来没想过改善品味,或者说为改善品味做点努力,即便装模作样的迎合也没有,所以他才不反对克鲁姆夫人对他的评价,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确实“俗不可耐”。
但是现在,他很想为自己无意间撞破的大自然的瑰丽证明点什么。让他即兴创作纯属天方夜谭,背诵点什么总是可行的。当他兴致勃勃的搜肠刮肚,想要找寻能够借用的贴合此情此景的诗歌后遗憾的发现肚子里的墨水显然不够用,竟然没有一句能够派上用场。
窘迫维持了三秒钟……
斯图鲁松室长45度角虔诚仰视的头迅速转为稀松平常的目视前方,返过身去琢磨是不是应该再报个平安,一边想一边掏出了魔法小镜子——所以说斯图鲁松室长是个想得开的人。
镜子刚拿出来海姆达尔马上意识到眼下的时间点,刚要搁回去,镜面涟漪圈圈的晕开一团光,威克多的脸出现在镜子里。
海姆达尔老激动的,刚刚装深沉失败,沮丧的末梢还没从他脑海中完全退散,这个时刻和老爷灵犀。原来威克多一直惦着他,还没睡。
海姆达尔觉得他被治愈了。
【什么时候回来?】威克多开门见山。
“我已经看到庄园的房顶了。”海姆达尔扬起镜子对着掩映在林中的庄园晃了晃,怕威克多不相信似的,嘴里说:“看到没?看到没?”
实际上一点都看不真切,但是威克多还是睁眼说了瞎话。
前方一道黑影迎面蹿来,海姆达尔一个不查被扑个正着,惊叫声来不及发出就发觉黑影顺着自个儿的身体往上攀,最终落在肩膀上。
是豆荚。
海姆达尔的惊呼卡在喉咙里,憋的脸都红了,所幸背着光,他的窘迫不太明显。
【怎么回事?】威克多的声音从镜子那头急匆匆的冒出来。
“没事,豆荚吓了我一跳。”
威克多松了口气,【等会儿来我房间。】
海姆达尔用一种很深沉的口吻吩咐:“洗干净了在床上等我。”
老爷在镜子那头哈哈大笑,临了慢吞吞的回答,【宝贝儿,我已经在床上了。】
斯图鲁松室长差点就不淡定了,好不容易压下因为老爷的挑逗而被唤醒的内心的骚动,匆匆挂上“电话”。
[我是第一名。]豆荚得意的翘起尾巴,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
紧接着,前方道路上浮现出几道忽明忽灭的影子,随着影像轮廓的逐渐明晰,海姆达尔满脸笑容的张开胳膊,一副热烈欢迎的架势。
奶糖它们几个奔跑的更欢了。
小面包倒是很有骨气的没搭小八顺风车,迈着小短腿在地上拼命捣腾,奶糖和小八比她身高马大,一下就蹿到前面去了,小面包即便吊车尾也不气馁。
“国王呢?”海姆达尔随口一问。
[在睡觉吧。]豆荚不怎么在意的说。[下午保加利亚魔法部的人又来这里巡逻,它在树林里瞎转,差点和他们发生冲突,你没看见保加利亚的那几只嗅血被吓成什么样儿。保加利亚魔法部的探员不清楚国王的身份,还想把它抓回去,要不是威克多回来及时阻止,那几个探员的脖子大概要被它咬断了。]
“它受伤了没有?”海姆达尔忙问。
[不清楚……应该没有吧,晚上吃的挺多的,不过]豆荚犹豫了一下。[似乎没什么精神。]
这个时候,奶糖率先奔至面前纵身一跃,在海姆达尔的惊呼和豆荚“喵”的惊叫声中连人带猫一块儿扑倒在地。然后胸前霍地一沉,小八爬过奶糖的背跳到海姆达尔胸口,敦实的重量差点压得他一口气没提上来。
小面包终于跑到跟前,小绵羊似的弱弱叫唤着。小面包是雌性,还处于幼儿期,声线细幼,不像天生魁梧的雄性,小时候就具备了粗犷的雏形,奋力叫一声虽称不上震耳欲聋,却也是特别扎耳的。
小面包像颗肉团似的跌跌冲冲的往上跳,然后一个屁股墩落在地上。海姆达尔好不容易把奶糖和小八从身上扒下,给了小面包靠近的空隙。
他把小面包抱起来,小面包直往他脖子那里拱,海姆达尔只好把它抱的高些,这孩子自打生下来就喜欢贴着他的脖子,似乎这样让它有安全感。
奶糖和小八正兴奋着,就看见海姆达尔忽然脸一板,让豆荚也一并与它们同列,在眼前齐齐站好,几只动物不明所以,不过还是听话的照办了。
“为什么不睡觉?!”斯图鲁松室长又先甜后苦了,先前给了颗糖,这会儿开始训话了。
奶糖它们都垂头丧气的耷拉着。
豆荚是老油条,明白海姆达尔不过装装样子,他刚才看到它们那双炽热的小眼神儿以及那一脸的惊喜交加豆荚猫可都看在眼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