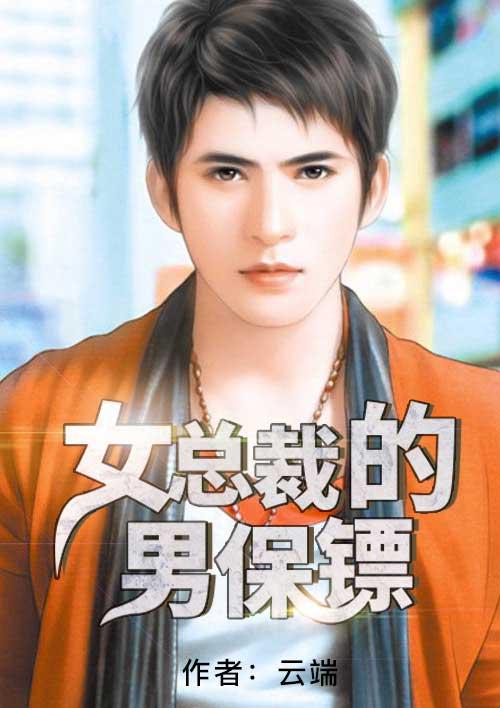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一手遮天一手捶地类似 > 第六章(第1页)
第六章(第1页)
宋郎生说,韩斐,是原来的驸马。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迎头截回牙关:“我和他成过亲?”
匪夷所思也该有个限度罢。
宋郎生道:“韩公子是在与公主大婚之日逃婚的。”
“逃婚?他倒是胆大妄为,如何逃的,后来有没被抓到。”
宋郎生斜眼,“这时候不是应该关心他为何逃婚么。”
我点头摊手,表示不再打断。
宋郎生说:“韩公子逃婚的理由,其实,我也不晓得。”
我:“……”
“因为他从未解释过。”
我想一想分析:“他会否和你一样也是被我胁迫逼于无奈才同意成婚,但因内心深处更有傲骨,宁死也不屈服强权,故而有此一举?”
宋郎生瞪着我没说话,脸上浮出一丝红意,约莫是气得不轻,苦于前一刻刚答应要“大气一些”,只得撑着抽搐的嘴角,从牙缝里崩出一句:“韩公子是在琼林宴时主动与公主示好,应是心仪的架势。”
我不由讶然:“如此说来他是对本公主始乱终弃?所以我一怒之下才把他拐到府内折磨他以泄心头之恨?”
宋郎生说:“公主大怒是真,不过当韩尚书领着韩斐求皇上赐罪时,亏得公主求情免于一死,这事才得以不了了之。”
我摸摸鼻子,“我那时没事吧?莫非是另有阴谋?”
宋郎生拉长着脸:“怎么公主似乎很希望自己心理阴暗么。”
难道不是?咳,当然不是。
我望着窗外有些刺眼的朝阳,和蔼地道:“本公主是被自己的境界感动了,就如艳阳在空无限美好。”
宋郎生将袖子抬到嘴边轻咳了一声,显然是被呛到了,我等了等,见他没回应,只道:“那后来,他又是为何入府做我的面首呢?”
“不得而知。”宋郎生道,“他先我进府,我对公主的事素来不多过问。”
话题进展至此就没接下去了。
其实我还有不少问题,诸如“韩斐平时在府中做什么”“我有没有招他侍寝过”此类,不过眼下这气氛确是难以启齿,日子还长,也不急于一时,姑且将疑问放上一放。
宋郎生贵为大理寺卿自不能成日在屋里陪我聊这些情感问题,用过早膳便出府了。
我闲来无事窝在书房里览阅那些看去翻得甚勤的旧书籍,熟悉一些今朝史料政事。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只是走马观花的扫去一眼,竟记起七七八八,不免有些令人惊喜。
传言襄仪公主殚见洽闻,斗酒百篇,看来此言流传的很是那么回事。
我查翻了两本通鉴纪事,又随手捻起书架上一本红皮书,面上未见任何字迹,正奇怪时又听来了侍女急急躁躁的求见声。
唉,为何公主府里的侍女成日都是一副如履薄冰的模样。
竟是又有来客,来得还是宫里的公公。
当这小哥儿穿着湛蓝色对襟长袍跨步入屋,我暗自喟叹这内侍不知入宫时是否净身没净干净,如此英伟的身姿只怕上战对敌都无不可,哪和太监沾上一丝边。
不错,这正是侍奉我那太子皇弟的年轻公公,成铁忠,贴身又忠心。
打我回府,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前面说到我弟弟担心我担心的不得了,可他身为太子政事繁忙,最近貌似又被什么江浙水患烦的脱不开身,故而一有贡品补药就让成公公给我捎来,这一来二往,我对他也有些熟络了。
所以他一进屋,我头也不抬的问:“太子殿下又送什么来了?”
成公公道:“高丽参。”
我说:“本宫火头正旺,不宜食用过多补品,回去告诉太子,再把人参鹿茸往我这搁,我统统拿去剁碎了敷脸。”
驸马说,这就是公主与太子说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