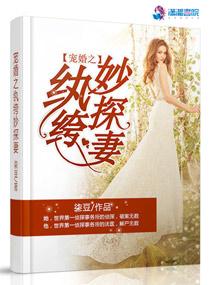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庶女重生世子我是你的妃阅读免费阅读 > 第九章(第1页)
第九章(第1页)
木容心里走马灯似的过着自己会见过的人,这一辈子,加上以前走过的那一遭,实在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并没有多少。前这十五年里都是困在太守府里的,可太守府里断断没有这个人的。倒也去城郊别院住过一旬,而城郊别院里使唤的都是些个婆子老妈妈,更是没有这样的丫鬟。而余下的那二十年,就只有上京的云家了。
木容眉尖忽然一蹙,她隐约想起,这丫头,是云家的丫鬟,且是一个到了三四十岁上了,还梳着未嫁女发髻的丫鬟。
可木容心里却忽然愈发的恍惚起来,她是记错了?还是这中间有什么差错?怎么云家的奴婢此刻会在峦安?还跪在衙门后门卖身葬主?还是说,云深眼下已然到了峦安?正是在这个时候买下了这个丫鬟?
木容心里忽的一颤甩了车帘,坐正了身子心便慌了起来。
可又想了一想,她眉头便舒展开了,断然不会是。云深看似平和,却绝不是好事之人,家中后院之事他从不过问,所有心思尽在朝堂之上人情往来,又怎么会多事的采买一个来历不明的丫鬟?
木容又略略撩起了些微窗帘,仔细去看那丫头露出的些微面容现出的神情,她必然是忠心的,否则又怎么会自卖葬旧主?可她眼下这神情却又太过古怪,竟是沉静的,漠然的,甚至于,带着几分凛然的冷冽。
木容记不清这人从前是在哪里伺候的,总归她是在云家后宅见过,且不止一回见过,只是这人却是忽然之间不见了,而在她不见之前,云家内宅里似乎隐约透出了一丝风声,好像是木宁受了些古怪的外伤,且还不轻。
木宁当年用尽心思,虽说没能把木容替换下来取而代之,可最终也算是遂了心愿的,在木容因重病被遣送到城郊别院将养的日子里,假做以婚书上云深未婚妻的身份与之相处,竟还生出了几分情意,正是这些情意,最终让云深难以舍弃她,是一并以平妻的身份也娶回了云家的。他们的这份情意加之这些事故,最终还被炎朝学子们冠以了才子佳人的往事,倒是颇受世人称赞艳羡的。
这人眼下在峦安,将来竟在上京云家,莫非那时在云家里木宁的事,当真和她有关?
鬼使神差,木容心下就是有这般的笃定,她忽然伸手抹下腕上带着的一副银镯,掂量了掂量这粗苯的物什也有二三两重,便又把头上的一根银簪也一并拔了下来。
“姑娘这是做什么?”
莲子看木容如此很是惊诧,还没缓过神来,就见木容一股脑把身上这只有的三件首饰都塞到了自己手里:
“去,把这丫头买下来。”
莲子显然一惊,可看自家主子神情似乎有些异于往常,她便顿了一顿再没说什么,将木容的簪子又别回她发间,伸手把自己只戴着的一支银镯子取下,这才又带上围帽,再度下了马车。
莲子是怕木容身上本就只戴了这几样首饰,若是回去都不见了,恐怕就要引人猜疑了。
木容急急又撩开窗帘去看,就见莲子上前递了首饰,人群中倒是忽然嘁嘁测测的一阵旁人议论,那跪着的女子倒是一派平静,缓了一缓接下三支银镯,随后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莲子,莲子接去一看,便是点了点头,回手一指马车。
那女子便顺着莲子手势看来,这一眼,却是让木容心底颤了一颤。
这眼神,就如她刚刚回来的时候一样,好似看透了人间生死,再没了任何念想,空的让人害怕。
马车晃了晃,莲子又回了马车,将手中的纸递了来,竟是那女子的卖身契,木容掂在手里只觉着有些重,可这女子却当真算是贱卖了自己,三支粗苯的银镯,不足五两银子。
她无意间便去看那卖身契,上面写着的名字,这女子,姓丁,名慕宁。
这名字,似乎隐隐也印证了什么。
木容合了卖身契,就见那女子起身,就近寻了家当铺进去,没过多久又出来,往街外去了,也是没过多久,就见了几个工人模样的男子来,将她旧主的尸身抬去,她交代了几句,将手里的几两银子也一并给了人。
“恐怕是棺材铺子的工人。”
莲子看了看,眼下也露了几许悲戚,似是被这姓丁的女子触动。
这一折腾,足足又耽误了差不多一两个时辰,莲子担忧马车停在这里时候久了引好事之人打听,就招呼车夫把马车赶到了得月巷,就站在周家附近的地方停了半晌,木容没了心思到周家就拜访,便也留在马车里,只好等下一回再说去周家的事。
约莫着到了和那女子约定的时候,马车才又回了衙门后门那处,果然见那女子立在原处等候,身上已然换了衣裳。
到底莲子嫌她丧气,不肯让她到木容跟前来,便让她跟在马车后面,一直又回到了木家西跨院的角门上。
木容下了马车等这人走到近前来,这才就着昏黄的光仔细打量了几眼。这丫头年岁已然不算小,有十七八岁的模样,倒很是眉清目秀,面上神情仍旧同那时一样,没有任何改变,眼底星点泪光也没有。
“你是周家我舅母送我的奴婢,记着你身份。”
趁着莲子叩门的功夫,木容忽然没头绪的交代了一句,这丫头怔了一下,随即应了声是,连声音都是那般的冷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