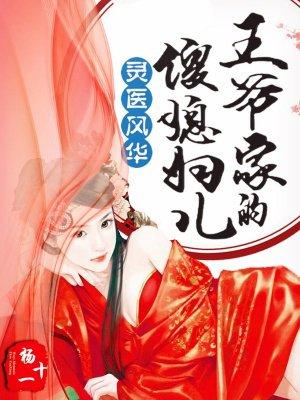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圣宋通宝 > 第60页(第1页)
第60页(第1页)
一个更猥琐的声音传来:“嘿嘿,蒙都头在县里也算雄壮的了,如今见了时大郎仿佛老鼠见了猫,偏偏褚姑娘一嗓子就能阻止他,难道这位时大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嘘,不要命了,他是傻子,听了这话,万一恼怒起来,不要说冲你给一拳,便是瞪你一眼,你能消受得起——这样的话都敢说,可不是一心寻死?!”褚素珍放下了帘子,刚才的闲言中把她也说到了,让她有点脸红,但她还要说:“瞧瞧,世人的闲言多么可怕……娥娘,环娘刚才是那个意思,你的心思比她还多,难道你……”黄娥的脸微微发红:“大郎在事发之后,一个月内大门不出,可不是为了我们,娥娘受救命之恩,怎敢妄自责备恩人?”褚姑娘放下了帘子:“我今天跟着来,只是想提醒你们一声,你们是劫后余生之人,如果你们因为这场劫难,反而鱼跃龙门,那你们收获的不再是同情,而是嘲讽——这就是人情世故。”稍停,褚素珍长叹一声:“世情的枷锁谁能挣得开?女人这辈子,怎能不小心翼翼?”黄娥眼珠转了转:“娥娘年纪小,原来不知道人情世故,但看到褚大姐仅凭满腹学才,在海州城呼风唤雨,却也如此畏谗怕谤,不禁心有戚戚焉。”褚素珍长叹一声:“子非鱼,焉知鱼之忧?”宋代的社会风气秉承唐代,更多少带有一点五胡乱华时代胡人带来的风尚,这个朝代比较开放,而整个大宋朝百分之七十的赋税来自海外商贸,所以开放的气氛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当中。这时代更是中国市民阶层诞生的年代,市井百姓对外来事物的态度,连现代社会都自愧不如。这时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也多是自由恋爱,从宋代几位女诗人的记载当中,她们换男友简直像换股票一样,丝毫没有心理负担,合则留不合则去。然而,即使是现代社会,这种行为也免不了遭人议论,宋代的褚素珍虽然率性而为,她承受的压力也是有的——多少言词尽在这一声叹息声中。……午时,妙泰道姑所属的崔庄,庄农很诧异的望着这两辆马车驶进庄子。雨后不久,地面还湿润着,车辙在门前留下深深的印记,这车辙很新鲜,很独一无二,更衬得崔庄有点“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味道。时穿跳下了骡车,没等他开口,庄农已经紧着喊:“时大郎来了,我琢磨着这几天你也该来了?”什么叫“该来了”?我也成了名人?!其实,我这么热心,也不是天生喜欢拿好人卡,我只是在享受作弊的乐趣而已。来到宋代开金手指,太有趣了。紧闭的大门轰然开放,两辆马车长驱直入,妙泰的女使站在廊下,欢快的迎接时穿:“时大郎来了,这几日,姑娘正琢磨着,想借时大郎这尊大佛震一震海州的浮浪子,这下可好了,天随人愿。”心若有善就是佛褚素珍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娇嗔的抱怨:“小红,我呢?好歹我也是跟妙泰姐姐几年的交情,怎么你眼里只有时大郎,没有我?”小红脸色一红,褚姑娘这话说得暧昧,这话要是别人说了,小红肯定反唇相讥,但说话的是褚素珍,一方面知道对方说话有口无心,另一方面畏惧对方的名气,小红干脆装不知道:“哎呦,门房通报只有时大郎,没想到褚姑娘也到了,我回头一定责骂一下门房——不知道这是女人的庄子吗,怎么眼里头只有时大郎,没有褚姑娘?”“可别——”褚姑娘马上掩饰:“我如今的名声已经够臭了,这次再让人知道跟时大郎结伴而行,那闲人不知道该传成什么样子了?”小红作揖:“褚姑娘别取笑我们了,崔姑娘正在门里等,耽搁了你们,我可要挨骂了。”小红是女使,“女使”跟“使女”仅仅是字词顺序的颠倒,一下子就跨越了两个时代。前者是雇佣的打工妹,后者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前者是唐宋,后者是明清。小红是崔府雇用的自由人,她跟崔府签了十年雇佣合同,期间,崔府的小姐出家做道士,小红因雇用合同没满役期,也跟着崔府小姐——也就是妙泰,进入庙里伺候妙泰起居。入乡随俗,她在庙里也换上道姑的工作服,现在妙泰回到自己的农庄,小红也恢复了俗家打扮。恢复俗家打扮还不算什么,关键是她称呼妙泰方式也改了,以俗家本姓称呼妙泰为“崔姑娘”。褚素珍沉吟着往门里迈步,边走边思索小红称呼的变化,这变化意味着妙泰的新身份吗?回头望,时穿对称呼的变化毫无感觉,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小红已经改成俗家打扮。黄娥从小生活在勾心斗角的环境,对人情世故的变化最敏感,每到一个新环境,她顿时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出任何纰漏。这时,她觉得有蹊跷,而时穿这个人间过客,很冲直撞多少年,不屑去纠缠家长里短,他一脸坦然与不在意的向里走着。黄娥则揪起了心,她快速走了几步,超越了时穿,见了妙泰后,她抢着上前,揽过打招呼的事,抢先对身穿俗家衣服的妙泰致问候词……但寒暄过后,时穿还是说错了话,他张口就说:“我听说桃花观发生了失窃案,妙泰师姑没受到骚扰吧?”妙泰含蓄的笑了一下:“奴家听说这桩失窃案已经取消了,没错,观主最终取消了报案,目前正在四处寻找木匠师傅,准备重新雕刻三尊神像。”黄娥在一旁,解释说:“我哥哥听蒙都头……现在该叫蒙县尉了,听他说桃花观发生了失窃案,又听说师姑已经离开了桃花观,担心师姑受到波及,所以赶来探望……”妙泰用手帕掩住嘴,纠正说:“你叫我崔姑娘吧——奴家已经离开了道观,桃花观里的事情跟我再无关系,我已经不是桃花观里的妙泰了,这事情怎么能牵连我?”说到这里,崔姑娘忍不住笑出声来:“说来好笑,三清道祖的三尊像,怎么偏偏没了两尊,留下那一尊却让人捉摸不透,也不知道凭啥这尊神还肯停留在庙中?啐啐啐,百无禁忌……咯咯咯,说起来挺逗人的,我庙里有相熟的人把这事告诉我,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都笑了一天了。”时穿先是愣了一下,反问:“你好歹也在庙里住了那么久,烧香拜神的,应该很虔诚的吧?神像没了,你一点不感到……不感到信仰天崩地裂?”妙泰慢慢敛起笑容,歪着头想了想,平静的答:“都过去了,我刚被赶出庙观的时候,确实感到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神佛原本是引导人向善的,为什么我一心向善,却落得如此结果,为什么神佛眼看着那些人就在神像眼皮底下作恶,却依旧沾花微笑。而我呐,我仅仅存一点小小善心,却不得不闭门自守,生怕覆巢之下。神呐?佛呐?当姑娘们哀哀哭喊的时候,神佛何在?当人们跪倒在它面前,苦苦求告的时候,神佛何应?……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全放下了。天地之间岂无神焉?借你之手,神佛已经惩罚他们了——神不在他们那里,不在那尊木偶凡胎上面,神行与天地之间。若本心向善,我便是神,若心中有恶念,那已经是魔了。所谓‘立地成佛’,大约说的是本心向善,顿时成佛!如此,又何必着相?”时穿神色一变,站起来郑重拱手:“崔姑娘,我服你!你真是个……你真诚的信仰,让我自惭形愧,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这样满怀坚定信仰的人了。过去的信仰体系崩塌了,许多人要死要活的,你却放下执念,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心情,从此天地开阔。好笑我,本来担心连累了你,本以为你避到乡下,会苦闷寂寞,却没想到,你身居陋室悠然自得,倒是我,用世俗的想法揣测你,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