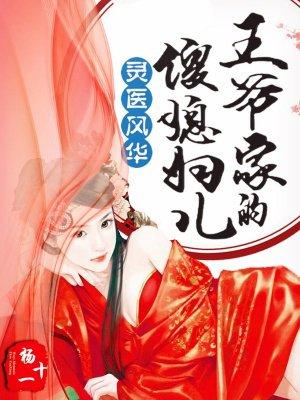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从业几年 > 第41页(第1页)
第41页(第1页)
薛嫔连忙跪下:“臣妾失言,陛下息怒!陛下息怒!”
“潘相乐此等忠臣,才配得上司徒一职,你父亲又是什么东西?竟也敢肖想在朝堂占一席之地?”,高洋制住薛嫔,抓下她一缕又一缕的长发。
黑色发丝漫天飞舞,他狰狞大笑:“你父亲为我北齐做了什么?不过是生下一个秽乱宫闱的贱妇罢了!”
薛嫔吓得大哭起来:“臣妾没有!臣妾从未秽乱宫闱!”
“哦?”,高洋的动作突然停住:“是吗?”
“那你来看看这个!”
他快步走到屏风边,拉开其中一扇,露出一张紫檀画桌。
画桌上赫然是一颗血迹未干,死不瞑目的人头,因被斩下的时间不长,人头上的须发清晰,历历可数,面貌更是容易辨认——正是清河王高岳。
高洋指指薛嫔:“你…”
指指人头:“和他,有没有私通?”
薛嫔看到人头,双膝一软,瘫倒在地,再说不出半个字。
她凝视高岳枯涸的双眼,扑簌簌落下泪来:“是臣妾对不起殿下,是臣妾拖累殿下…”
高岳垂涎薛嫔美色,薛嫔又不堪忍受高洋性情反复无常,两人瓜田李下,珠胎暗结,清河王手里有兵权,高洋投鼠忌器,才隐忍到今日,高岳死前已经认了罪,薛嫔却不知悔改,她爬到画桌边哭闹不休,如同是高洋强行拆散了她与高岳一般。
高洋细细抚摸着人头上的每处伤口,对女人的哭喊置若罔闻:“我已经处置了他,现在轮到你了。”
薛嫔浑身一个激灵,她是最了解高洋的人,高洋手段残忍无比,平时以杀人取乐,一想到要受那些可怖刑罚,她的神智被推到崩溃边缘,拼命求饶:“求陛下看在臣妾昔日的好处上,赐臣妾一个干净的了断吧陛下!”
她尖叫着抓乱了自己的发髻,顶着满头乱蓬蓬的珠翠,抱住高洋的小腿嘶叫:“求陛下开恩!求陛下开恩!”
高洋耐心告罄:“拖出去!”
他既下了令,薛嫔深知求也无用,说话调子一转,哑声唱起两人初见时的那首歌谣:
“杳杳灵凤,绵绵长归。悠悠我思,永与愿违。万劫无期,何时来飞?”
唱罢,她想起往日两厢情好的时光,声音哽咽:“无论陛下如何处置臣妾,臣妾永远记得那一日的陛下,记得那一日的小雨和凤凰花。”
展枫玥是毋庸置疑的美人,当她泫然欲泣,用充满情意的眼神盯着李郁时,李郁绝非全无感觉,在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相识十几年,友情深厚的朋友。
展枫玥还在戏里,她抱住李郁的腿,好像在苦苦期待着什么。
李郁看了一眼展枫玥的表情,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崩溃了,猛地抬脚踢开她。
“不行,这我演不了。”
李郁留下一句话,匆匆拂袖而去,刚才他那一脚没收住力气,展枫玥被踹得滚下台阶,她伏在地上,又是屈辱又是难过,分不清这是戏里的情绪还是真实的感觉,心乱如麻,等不及尚轶轩发话,也顾不上肉体的疼痛,摇摇欲坠地站起来,闷头追了出去。
两个主演一崩,现场立即一片哗然,说什么的都有,内容无外乎关于一个“情”字。
尚轶轩沉着脸不说话,反复观看刚才展枫玥演崩的一段,仰头灌了一大口矿泉水,快速选中几个镜头,和身边人说:“这些剪了,其他留下,我要用。”
负责场地统筹的工作人员上前请示:“尚导,A组刚才来电话,他们也要用这个景,现在已经快到了。”
“行,知道。”,尚轶轩无暇理会这些琐事。
他站起来,一丝不苟地指挥现场:“都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把主演找回来,我们接着拍。”
李郁一口气跑到海岸边,他踹完那一脚就后悔了,正琢磨着该如何负荆请罪,负荆请罪的对象就出现在了身后。
“你怎么来了?”,李郁大惊。
展枫玥满面泪水地扑上来:“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A组副导演叫陈录,是尚轶轩的侄子,大学刚毕业不久,为人风趣,又很会说话,拍完这场在水边的戏,陈录反复夸蜷川表现力好,蜷川都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买了一打鱼饼分给群演,还给陈录留了一个:“其实拍电影挺好玩儿的,没我想象得那么苦。”
蜷川刚把鱼饼塞进嘴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哎你们看!B组的人怎么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