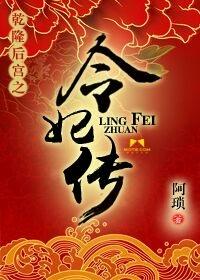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前妻来找我我该怎么办 > 第151章 天生傲骨咱不会呀(第1页)
第151章 天生傲骨咱不会呀(第1页)
回到家,沈父坐沙发,沈母好像害怕他们跑了,关上门回来,先把哀怨的潘多拉关卧室,然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得离门口近一些的位置。
姜惟伸手帮她,也被她黑着脸拒绝了。
沈在心就拉着姜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二人又那那种鬼混过的模样,至少是让沈父看着厌烦。
沈父说:“问你们呢,你俩都是给我说,你们是朋友,朋友,普通朋友,一起合作做生意,这像是一起做生意的普通朋友,衣冠不整,手还牵着手?”
沈在心这才注意到。
还真是,手还在牵着呢。
也得牵下去呀。
你丢了,姜惟怎么办?
在自己家里,被两个长辈无缘无故凶一回?
自己现在是她的胆量和依靠呀。
沈在心硬着头皮说:“爸。依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婚姻存续期间跟姜惟才好上的,而且发乎情,止于礼,今天是彻底离了,姜惟才去我那儿,做一桌好饭,买了点酒,等我回家的,说实话,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刚喝完酒,抱着她亲吻,所以我知道,现在不定哪还有着口红,真要长期勾搭,绝对也不是今天仓惶回来的狼狈相。”
沈父气笑了:“真是自从开始做生意,这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我还没问呢,你就先理直气壮地说你没错了。“
他说:“你离婚,你就没有错?”
沈在心没吭气。
沈母问:“我就问你,谁让你离的?你离婚你没错,你捂那么严实干什么?你不心虚,你为什么说都不跟家里说。”
沈在心说:“怕你们不愿意呀,给你们说,你们是同意呢,还是阻挠呢?肯定说,在心,结个婚不容易,成个家,两个不认识的人走在一起,谁没有点儿矛盾?这是哄你,哄你没用,你那鞋,我爸的那皮带都等着伺候,我敢说吗?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和平分手,是觉得双方不合适,你看,我回余市了,她人在浒市,他家里他爸他妈也一直嫌我,老这样是办法吗?不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一起把话说开,就和平分手了。”
沈父敲着茶几说:“我就问你,谁说开的,谁提出来要离婚的?”
姜惟脱口道:“尤雅。”
沈在心则脱口说:“我。”
几乎是异口同声。
沈在心看向姜惟,姜惟是怕他挨打,没办法,改口说:“我觉得是尤雅。”
沈母已经忍不下去了:“你?你要说尤雅找你离婚,人家看不上你,这还有情可原,咱剃头挑子一头热,只能随她,跟她离了就离了,你凭啥跟别人离呢,你是有钱,你是有貌,还是你有个小医院,你直接飘了,以前你就跟我说,人家尤雅这样,人家尤雅那样,你们根本过不下去,结果人来我们家,一对质,你是哑口无言,你不说人家的问题了?”
沈父苦恼地抓抓头:“还说这些干啥呀,离都离了,离婚这么大的事儿,过年你俩就说好了,这多久了,一个月了,你能没事儿人一样?过年的时候,你还带着她到处走亲戚,谁忘了给你们红包,你还张嘴要……”
沈在心连忙说:“红包都在我这儿,主要是我开医院,手里没钱,带着她,哄着亲戚给点压岁钱。”
红包?
当然不在他这儿。
尤雅当仁不让带走了。
这是怕沈父沈母觉得人家尤雅骗红包,自己又揽下来了。
沈母问沈父:“咋办吗?你说一声呀,我们劝尤雅两句,弄个这?你把人恨的,恨的!”
鞋脱了。
对着沈在心就砸过去。
沈在心也没敢躲,连忙说:“我也知道我有问题,我也知道我有错,我也在反思,我就觉得我这个性格
吧,它就是那种喜新厌旧的性格,你们不知道,回来之后,有个医院的女孩,我也忍不住勾引过,最后啥事儿没干,就是我一想,我结婚干什么?这不是被婚姻束缚着呢。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就现阶段还不适合跟人结婚,一天到晚光想乱找,想象着去哪寻新鲜寻刺激,我就给尤雅说,你答应我,放我一马,从此天高地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