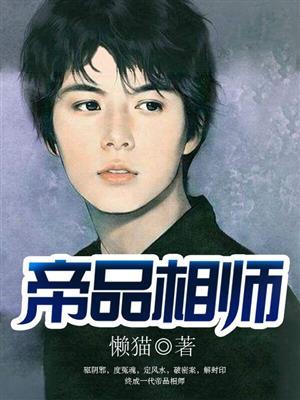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颜如玉个人资料 > 第76(第1页)
第76(第1页)
他本意是想要来随便瞧上一眼,看蓝田写到哪里了。可是走到身边低头一看,一刹那间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整页极为辣眼睛字迹,一时之间居然是看不清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
蓝田自然是知道自己写的字如何,开口解释道:“我只是着急把脑内剧情先写下来,之后会誊抄的。”
褚安铭语气略带嘲讽:“本王实在是担心到时候连你自己都看不清这写的是什么?”
蓝田提笔沾了些墨水,低下头继续在稿纸上鬼画符,口中说道:“那就请王爷不要看着我写,以免蓝田手下紧张,真写出连自己都认不出的字来。”
他听见褚安铭轻轻笑了一下,又在自己身边占了片刻方才离开,临走还从书案上顺走一支笔和几张稿纸。
褚安铭离开桌边后,蓝田也自在了许多。他整理了一下刚被打断的思路,继续埋头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将方才刚起了个头就被打断的两位主人公鱼水之欢的内容给写了个酣畅淋漓。
“马车内,王爷为受伤的将军上药。
颠簸的山路,吱嘎作响的车厢,拉车的马儿耳朵动了动听见了后面传来隐约的低吟声响。
…………”
一段话写完,落下了最后一笔的蓝田咽了咽口水,才发现自己胸口狂跳,脸上滚烫。
他心虚地抬眼看了不远处坐着的褚安铭,生怕被那人看到自己脸上通红的模样。还好褚安铭并未朝他看过来。褚安铭此刻正一手执笔,一手那着一张已经被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稿,紧紧皱褶眉,表情凝重似乎被什么繁复的事情给困扰住了。
蓝田轻手轻脚地放下手中的笔,伸手要端桌子上已经凉透的一杯茶水,想靠这冷茶平一平心中拿把火,别让褚安铭给瞧出什么异样,到时候又要被阴阳怪气一番。
可大概是因为写字的时候实在用力,不知不觉间手中竟然出了一层滑腻的手汗,于是蓝田一个没拿稳,水杯竟然从手中滑落,应声落在了地上。
褚安铭的思绪被这动静从琐事中拉回,睁着眼看向蓝田。看到他满面潮红,一双如受惊小鹿般的眸子上眼睫忽闪着,时儿看向地面,时儿又心虚地看向自己。
褚安铭刚才在想那日徐夫人同他说的张家丝绸生意的困境。就算不是为了思远,只因徐夫人是有功之臣的遗孀这一点上他也是要出手相助的。这些日子,他一直没得功夫静下心来好好算算需得多少银子才能助张家度过现下的窘境,方才细细想来,却发现这问题似乎并非是资助几次银子便能解决的事情。
他是知道织造局为什么会要求今年增加一万匹的订单的。去年燕王在北疆替皇上收服了蒙族八大部落中的呼延部。皇上今年除了要增加对燕王的封赏外还要对呼延部也赏一批丝绸用以收买安抚。织造局虽然每年都会对丝绸生产和采购订单留有余量,但这多出来的数量实在太多,他们自己的织机加班加点也赶不出那么多匹,自然就把压力加到了下面的丝绸商这里。丝绸商人毁了别的小单子一次,留下织造局的大单子也是无奈之举,虽在今年的帐目上有所损失,但织造局的订单对民间丝绸商来说就是又赚钱又赚吆喝的买卖,对于之后的几年也算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能确保明年依旧能满足织造局在原有订单基础上增加收购数量的需求,丝绸商可能会提前去别处收货用于备货应对,今年流通在市面上的丝绸本就有一部分被织造局收走,剩下的数量不多,丝绸商收货的价格也会偏高,备货成本本就高出原先。
可若是到了明年,织造局并未增加需求,那多丝绸商手上多备的货必定是要拿到市场上售卖的。接了织造局的订单的丝绸商不止一家,多家丝绸商同时放货,丝绸价格必定会下跌,甚至于为了尽快回笼资金,许多丝绸商不得不低于成本价出售手里的丝绸。那到时候就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明年织造局究竟会从民间收多少匹的丝绸,但现在谁也不知道。
所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终都压在徐夫人堂兄那样的丝绸商身上,只是这风险又必须担着,不然失去製造局的打单子,生意也没法做下去了。所以,徐夫人才会说“明年不只要如何了”。
褚安铭想不出什么能帮到她的法子,毕竟连皇上都无法预测明年的丝绸需求,谁知会不会又有新贵需得封赏,又有新的小国来寻求大昌的庇护。
但若是到时候直接给银子资助,他怕徐夫人不愿收下,他琢磨着是否到时候找个由头,用较高一些的价格能将张家手里多余的丝绸收走,但又担心这收来的丝绸要安置到哪里去。
思来想去许久,各种方法和算法不知不觉写满了一整页,可就是觉得无论何种方法都还是有许多不妥,褚安铭发现自己在这原本不觉得很暖和的屋子里,竟给急出了一层薄汗来。
直到听见“哐当”一声,杯盏落地,他抬头便看见有个好看的人儿坐在那里,一脸惹人疼爱的受惊模样,顿时心中一软,那一团乱麻似的思绪被暂且放了下来。
有些不确定的东西令人烦躁,有些製造不确定的人却十分有趣。
褚安铭歪头对蓝田道:“怎么那么不小心?”
蓝田知道自己脸上的燥热泛红还没褪去,只是不知褚安铭有没有看出异样,低下头有些局促地回:“手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