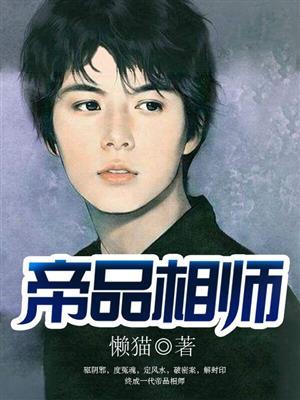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响尾蛇镇by > 第3页(第1页)
第3页(第1页)
“那小家伙挨个把我们看了一遍,小眼神儿可震惊了,他那大嗓门儿能把死人给闹活了。我知道,刚生下来的小孩儿哭得越响越好。可我还是总想着,那孩子长大以后有没有对他那‘生’不由己的人生灰心丧气过呢。”
车里静悄悄的。大约过了十分钟,或者一刻钟,汤姆清了清嗓子。“你在别处还有什么人吗?亲人?”
问题简单,答案复杂。吉米说:“算没有吧。”
“我也是。没了。虽说有过。你多大?”
为了回答准确,吉米在脑子里算了算。“上个月满四十三了。”他没庆祝——没人陪他庆祝。妈的!他想不起来最后一次听到别人对他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他许多年没跟人走得那么近了。
“那还来得及。”
“来得及?”
汤姆猛咳了一阵才回答。“听我一句,吉米。哪天你要是变成我这样的老不死,可没后悔药吃。是时候了。你得想办法拉自己一把。趁着还有机会,赶紧。”
吉米的胸口一阵刺痛,但他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我挺好,只是漂惯了。受不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不走不行。没觉着这样不对劲。”
汤姆哼了一声。“只要你开心,是没啥不对劲的。你开心吗?”
吉米没有回答。
又走了几英里,汤姆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他摩挲着那张纸,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吉米用余光看见他把它展开,尽管车里很暗看不清字,他仍对着那张纸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汤姆又把它折好,塞了回去。
“我有过一个儿子。”汤姆的声音很轻。“还住在响尾蛇镇的时候。我爱那孩子。但我恐怕更爱酒瓶子。我在他还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和他妈妈,再没见过。”
吉米在开车,不然他一定会紧闭双眼。他眯起眼,保持目视前方。他们正沿着一个缓坡开向特哈查比山口。“他今年多大?”吉米喉咙发紧。
“不知道。”汤姆又咳了一会儿。“成年了。”
“那你现在去响尾蛇镇干嘛?”
“害病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心里揣着对他的亏欠吧,跟长癌似的,一天比一天厉害。我给他写了封信,本来想寄给他,但是没有地址。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镇上,也可能早搬走了。可我没法把这破信给扔了。试过,扔不下手。我就打定主意自己把信送到。要是他还在那儿的话。”
希望如同鸩酒。吉米心想。初生的希望,灿若晨星,甜如蜜糖;但日渐消磨,遥遥无望,于是腐坏变质,暗生剧毒。所以他从不放任希望萌生。
“祝你找到他。”吉米说。
汤姆叹息着答道:“嗯,就算他恨透了我,我还是盼着见他。他吼我,骂我,都没关系。我就是想见他一面。”他调整了座椅靠背——吉米惊讶于那玩意儿居然还能往后倒——闭上了眼。
吉米又吞了一大口咖啡。
***
跑上坡路时,福特的响动变得更大了。它咣里咣当地抱怨着,让人心惊肉跳。吉米放轻油门,希望接下来的下坡路能让它心情好转。但并没有。它滑下山坡进入农田,穿过举城沉睡的贝克斯菲尔德,向北开往99号高速路,嗓门儿越来越大。
吉米一般不为车操心——坏了拉倒。他之前的车都是这样就扔了。他可以在路边拦顺风车,要不就留在当地打工,直到攒出一张车票的钱,或者再买另一辆破车。就算车坏在凌晨也无所谓,这一带不算太冷,来来往往的大卡车也多得是。可这次他有目的地,还有一位乘客。他真心想把汤姆送到响尾蛇镇去。
他继续往前开。右侧的天空开始泛白,虽然太阳尚未从内华达山脉的另一侧升起。这破车的噪音活像一场蹩脚的音乐会,吉米心想。打击乐太抢戏,吉他手们在为曲目争个不休。他在脑子里编着歌词,免得不留神睡过去。还能咋整,倒霉透顶,这破车就这么任性。前路漫漫,心有不甘,九十九号公路我他妈还没走完。好吧,那啥,他可没说他是个音乐家。
虽然车头的噪声和他脑子里的杂音吵成一片,吉米还是开始眼皮打架。到响尾蛇镇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车倒是问题不大,但他好像扛不住了。他得睡一会儿。车行至弗雷斯诺南郊,一个休息区出现在前方。他松了口气,满怀庆幸地下了高速。“我得打个盹儿。半个钟头就行。”
汤姆没吭声。
停车场的一头聚着几辆卡车,厕所旁有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除此之外空荡荡的。高处的探照灯被关掉了,晨曦昏暗朦胧。吉米在一个远离其他车的位置停下,熄了火。福特又嚷嚷了几句,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这才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