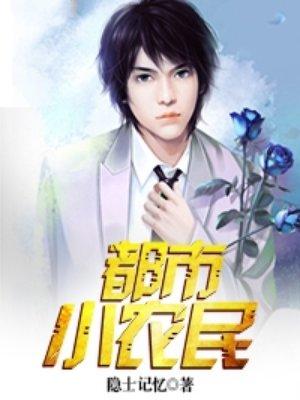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只怕酒醒时候 > 第86页(第1页)
第86页(第1页)
文贞问,“殿下当真不跟我们走?”
琅邪“嗯”了声,看着他。
文贞睁大双眼,脸上还沾了些煤灰,“为什么?白姐姐说,殿下在这京中也并不安全,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他只是个孩子,琅邪对着他,倒比对着白青青坦诚许多,“我还有事要办。”
文贞不死心,“那殿下办完了事,会来找我们么?或者,我们安顿好,我就来找殿下!”
琅邪笑了一笑,“当然可以。”
他这时笑容似乎太多了。文贞觉得奇怪。但他也说不出哪里奇怪,只觉得好像琅邪已经完全原谅了他。
他呆呆看着琅邪侧脸,没头没脑地问了声,“殿下,我学的可像?”
“嗯?”
“我学那个人,学得可像?”
琅邪愣了愣,失笑,“傻孩子。”
他顺手便替文贞将脸上的一块锅灰抹掉了,“往后别再回来。”
天果然已全黑了。
他没走正门,飞檐走壁之间,但见府门口停了一顶软轿,还有几分眼熟,但也未作多想,三两下溜进院子,又从窗口滑进房去。
一身脏衣刚换下,忽听外间有人敲门,“殿下,您可醒了?”
“福伯?”
“!!!”福伯连忙推门进来,委屈得几乎飙泪,“您可醒了!”
他左右检查琅邪身上,并未发现新伤,方才放心,“那位在外头等了足足一个时辰!小的几次壮胆请他回去,他却不肯,硬要等您醒来!殿下,您这不声不响又睡这一日,小的真是害怕呀!”
琅邪汗颜,一边朝着廊下走,一边随口地安慰人,“慌什么,子帆又不是外人,怎么就被你说的跟洪水猛兽似的,还要壮胆才敢跟他说。。。。。。”
他那声音戛然而止,动作也顿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