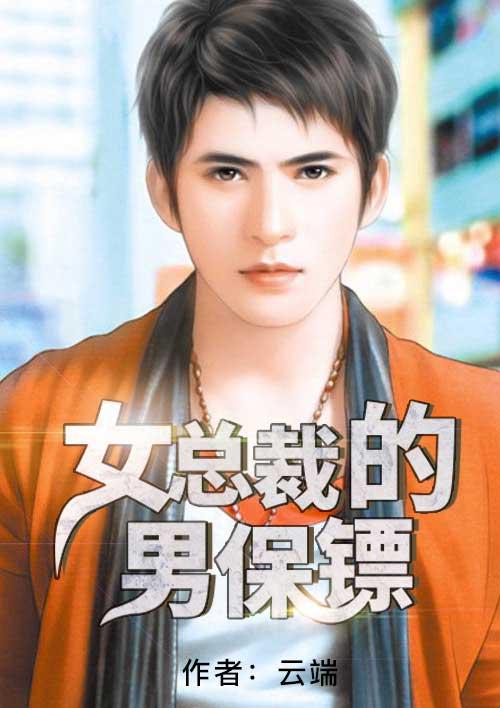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解药番外巫哲txt百度 > 第34页(第2页)
第34页(第2页)
“你买这么多盐干嘛?”他无奈地问了一句。
“等着哪天来个沙画艺术家给我画画。”江予夺坐下。
“改天吧,”程恪说,“我现在不想画,我有点儿晕。”
“不,”江予夺的回答很干脆,“就现在。”
“为什么啊?”程恪抬起头看着他,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因为,”江予夺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我不信。”
“嗯?”程恪还是看着他。
“别想随便编个瞎话蒙我,你现在就画,”江予夺声音有点儿冷,“画不出来别想出这个门,不画也别想出门。”
程恪对江予夺这种时冷时热的态度已经震惊不起来了,加上这会儿他脑子有点儿晕,他就只是不爽。
不是不爽江予夺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就大半夜的强迫他画沙画,而是江予夺不相信他会画沙画。
虽然家里人都不屑,觉得他玩这东西也就是个玩,没什么水平,但他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儿,否则许丁当初也不会托刘天成来请他。
这是他废物生活里唯一的亮点,让他没有最终完全沦陷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的唯一亮点,哪怕他自己一直也都没特别当回事。
“开灯。”程恪站了起来,在桌上摸了摸,挺光滑的。
江予夺起身,过去把灯打开了。
猛地亮起的灯光让程恪有一瞬间的迷茫,这事儿要搁以前,他也就一笑了之,他活得再没用,也犯不着因为一个八八六十四杆子都打不着的人的否定而生气。
也许今天两顿酒烧的吧。
他往江予夺身上扫了一眼:“穿衣服。”
“你画你的,你管我穿没穿衣服呢?”江予夺站着没动,拧着眉。
“这是起码的尊重,”程恪胳膊撑着桌子,看他还是站着没动,提高声音又吼了一声,“你他妈穿不穿!”
“操!”江予夺被他突出其来这声吼吓了一跳,指着他瞪了半天才转身进了卧室,“我穿上了你他妈要是画不出来,我就立马脱裤子把你干了!”
“我要是画出来了呢?”程恪感觉自己借着酒劲,对于江予夺时不时就奔下三路去的习性已经无所谓了,慢条斯理地拿起一袋盐撕开了口子,捏了点儿出来,在指尖搓了搓。
“免你仨月房租。”江予夺在卧室里说。
“我不差那点儿钱。”程恪把桌上的东西都放到了茶几上,这桌子是黑色的玻璃面,还挺合适的。
“口气挺大?”江予夺说。
“废话,我画不出来你都要干我了,”程恪说,“我要画出来就免仨月房租?是不是太不对等了。”
“行吧,”江予夺穿了条运动裤慢慢走了出来,“你既然这么想干我,那就这么着吧。”
程恪笑了笑,没再说话。
他其实不需要任何赌注,特别是这种他和刘天成他们一晚上张嘴就能说出二百五十种来的傻逼赌注。
“画什么?”程恪从盐袋里抓了一把盐出来,在桌上轻轻撒了几下,黑色桌子很快就均匀地铺上了一层白色。
“我。”江予夺看到程恪撒盐的第一个动作就知道他真的没有骗人。
就程恪这种家务废材,倒个水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是不是用错了一只手,但撒盐的这几下动作,却熟练而帅气,这种行云流水的流畅,一看就知道就算不会画沙画,起码也是有过三年以上撒尿和沙子经验的。
“你?”程恪抬眼看了看他。
“怎么,”江予夺也看着他,“画不出我复杂的英俊么?”
“先画个喵吧,我这一个多月都没碰过,”程恪低头用手指在桌上铺满的盐上点了一下,然后手指一带,划出了一条弧线,“手有点儿生。”
“嗯。”江予夺应了一声,盯着他的指尖。
第一条弧线之后,程恪有稍许的停顿,接着就是第二条,第三条,江予夺有些吃惊地发现,就这手指几下划过,他已经能看出这是个猫了。
程恪又用手指捏了些盐,在猫头上轻轻一旋,一个圈带中间一个小圆点出现,他甚至没看清盐是怎么从程恪指尖落下的。
接下去的“过程”对于他来说也不能叫做过程了,因为他根本看不清,唯一能看清的就是程恪从盐袋里捏盐,以及指尖所及之所被抹出的空白或是掠过的一条白色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