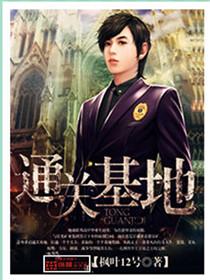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圆光观音的故事 > 第35页(第1页)
第35页(第1页)
公使从车马上下来看见“定国侯陈”的匾额不由怔了罗将军在旁笑道:“贵国的陈青竹将军,大人可熟悉?”
既封为“定国侯”,又是燮国第一的武将,在灵州与虞军鏖战月余,燮臣焉能不熟?但听罗将军这话,着实不知该如何回答,公使只好干笑两声又听罗将军赞叹道:“陈将军勇猛过人,罗某与他数次交锋,各有胜负;直至城破,将军战死,于乱军,尸骨无存身为武将,如此死法,当真是得其所哉……不仅罗某,连殿下也对陈将军钦佩得很呐!”
不论罗将军或殿下的钦佩是真是假,公使耳朵里嗡嗡响的只有“尸骨无存”四个字,只好流着冷汗又笑笑按二皇子的吩咐,罗将军每日和公使在一起,只是谈笑晏然,谦和有礼,但他所说字字句句,一多半地都是让公使明着赔笑暗着出汗也就只有罗将军这样善于辞令的儒将才能做到二皇子所说的“不要吓着他,也不要不吓着他”的要求,让公使日益敬畏,又不断了求和之心
进了府,内侍说殿下正用晚膳,也赐饭与罗将军和公使罗将军感激几欲涕零,即刻叩头于地遥遥拜谢山珍海味摆上来,席间罗将军高谈阔论,大讲每道菜肴的来历、原料、烹饪技法、该如何品尝滋味,乃至火候掌握得是否恰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忽而眉飞色舞,忽而摇头叹息,又连连劝酒,直听得公使茫然若失,简直不知身在何处如此一个时辰过去,天黑已久,府内各处灯火通明,隐约地还传来了女乐嬉笑的声音,内侍站在门口,垂眼尖声道:“殿下有请公使大人”
罗将军停了筷子,也停了谈笑,对公使道:“大人请,罗某就不送了”
“怎么……将军不同去么?”公使不禁惶惑,这几日好歹也和罗将军混了个脸熟,若这唯一的熟人都不在,独自去见二皇子,只怕尴尬时无人调和顿时公使只怀疑自己能否应对得当,被硬生生趸进耳朵里的鱼翅燕窝熊掌豹胎鲤鱼须猩猩唇,也都化作一团乌云,在脑黑压压地盘旋不去
“公公,不知殿下的意思……”罗将军问那内侍
内侍的音调高了几分,道:“殿下只请公使大人,没召将军不知将军欲见殿下有何贵干?”
罗将军也面带惶恐,向来的从容举止,见了二皇子身边的人竟是冰消瓦解,似乎立刻就会有霹雳当头打下一般,只战战兢兢连声道:“公公误会!公公误会!罗某实不敢冒犯”说着直给公使递眼色,道:“大人但请快去,勿要殿下久等”
公使随着内侍七转八拐,不知走了几十年才到了书房门口房内只有三人,二皇子象牙白衣,长发低垂,是极简单的便装,却于素净透露出无比端庄威严的气概他俯身查看面前案上铺开的一大张地图,右掌无意间正压在燮国皇都,左手食指慢慢地向右割出一道直线,起点看来像是在灵州,至于终点就不那么好说了一个红衣的妙龄少女坐在旁边,只目不转睛地看着二皇子,眉眼含笑,爱慕之情溢于言表,那是露蒹儿了她身后站着的是明春,虽不是盛装,但衣饰华贵,并且是燮国的梳妆,和露蒹儿的打扮大不相同
公使躬身作礼,二皇子抬头笑道:“免了!”神色温和,远不如公使想象狰狞但一念及罗将军方才的惶恐,二皇子越是温和,公使便越是心惊,不知他何时就要翻脸露出真面目二皇子看向明春,问:“这位大人你可认识?”
这话问得蹊跷露蒹儿亲昵地在明春肩后拍了拍,拿住了她的穴道明春本想狠狠地回一句“我怎么认识”,却觉得喉头一紧,舌根发僵,便再也说不出话来露蒹儿娇声俏笑道:“妹妹是陈将军养在深闺的乖女儿,怎么会认识什么臭男人?哎哟,对不住!贱妾失言了,公使大人莫要与奴家一般见识只是……哪门哪户都是有规矩的,想来公使大人也不认识定国侯家的小姐呀!”
她声音娇滴滴的,眼睛水汪汪的,身子斜斜地倚着明春,姿态妩媚慵懒明春被她捏得无法动弹,又说不出话,只气得发怔在公使看来,却是两个丽人亲亲密密他想:原来那是陈青竹的女儿!那女子喊她“妹妹”……听说陈青竹的女儿成了皇子的妾侍,看来不假,唉……
二皇子淡淡道:“再多说一字我割了你的舌头!”一句话只说得露蒹儿花容失色,连一个“是”也不敢应答,顿时收了风娆,直低下头去
“不知公使大人可做得了主?”二皇子依旧用那淡淡的口气说,“若做不了主,今日就不必麻烦了”
“我朝万岁授命下官……”公使道
“大人过来看!”二皇子听了这句就再不给公使开口的机会他的右手依旧压在燮国皇都,左手苍白的指尖在地图上从上至下缓缓地剜出一道弧这条弧线下来,公使身上流的汗比前几天和罗将军在一起时流得所有汗加起来都还要多,连明春在旁看了也只觉得喘不上气,背脊上一股冰凉潮湿的就倾泻下去了她忽然想曾有一次母亲亲手做了一盘红豆羹,那时年幼嘴馋,不懂规矩,用勺子狠狠地挖了一大块吃,惹得母亲接连几日地斥责而现在,明春的目光顺着二皇子食指那浅粉色杏仁形的指甲看下来,只觉得他也在燮国柔软膏腴的腹地上狠狠地挖了一大块,一样地贪馋,一样地无法无天,一样地放肆猖獗可有谁能来制止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