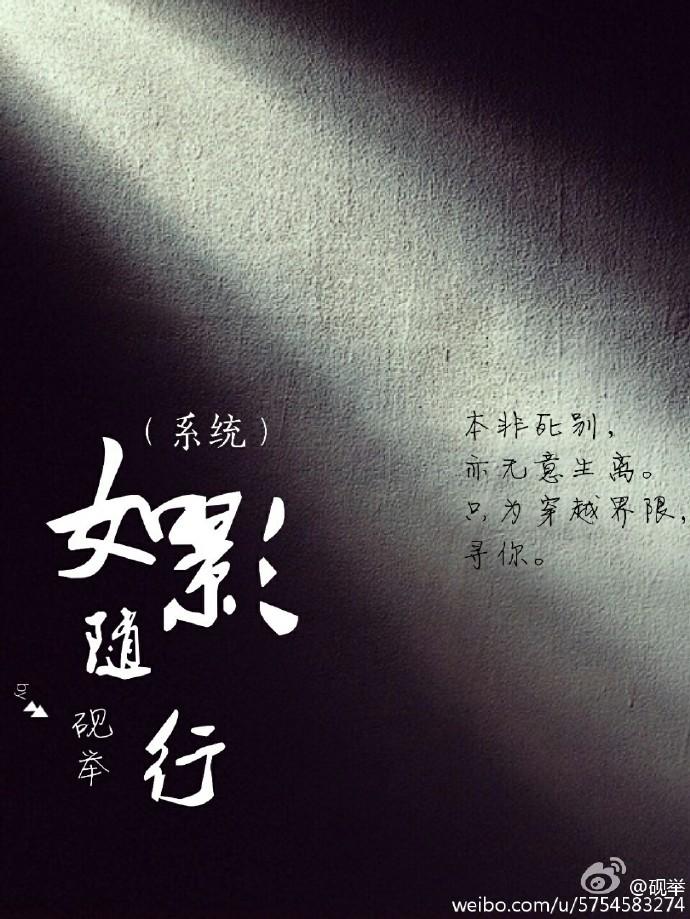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沙海原著汪灿角色介绍 > 第70章应激反应(第1页)
第70章应激反应(第1页)
随着通讯设备里的电路停止工作,电流发出的细小的嗡嗡声也消失了,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心跳声就显得格外清晰。
在场的除了汪灿,都没有机会能经常见到汪先生,尤其是汪十方,突然有资格直接和首领对话,难免有些惶恐,一直低着头就没抬起来过,紧张得像是要上台演讲,那叫一个心潮澎湃。
汪沛金倒是还好,汪先生一贯的说话习惯是中英夹杂,这也不是能让他随时提问的场合,他本来做好了听天书的准备,没想到这次通话时间很短,他几乎能听懂全部,这给了他莫大的鼓舞。
从摄像头前离开的时候,汪荧不经意地扫了眼汪沛金的脸,二人视线相撞的瞬间,后者不自觉就抖了一下。
——她依然苍白孱弱,如同易碎的冰雕,但是眼神中冰冷的压迫感令人窒息。
汪沛金忽然有些后怕,他见识过汪荧的实力,如果他刚才胆敢有什么逾越的举动,这么近的距离,说不定真会被她捏碎喉骨。
这样想着,他的心跳又开始加快,不过这次纯粹是因为惊惧。
汪荧察觉到他的心跳又发生了变化,无意关心他的心理活动,只是漠然地移开视线,退开前虚虚握了一下汪灿的手臂,轻声说:“你过来一下。”
说完,她径自走开,回到自己刚才休息的位置坐下,略抬了眼看人,倒像是一种无声的催促。
汪灿挑高了眉毛,一点头算是回应,示意汪十方他们自行休息,抬步便走了过去。
——汪荧刚才主动在汪先生面前扯下了绷带验伤,这时候的确是该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大概是先前的画面太过震撼,鬼使神差般,没有得到召唤的汪沛金也想跟过去,可他脚步才一动,汪十方就轻咳一声:“阿金,你来。”
汪沛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到自家搭档这边,但他仍不死心,抻着头总往那边张望。
汪十方恨铁不成钢,压低声音呵斥道:“你去干什么?他们欢迎你吗?”
他拍了拍汪沛金的后脖颈,强行让他停止窥探别人隐私的行为,然后一脸鄙夷地低下头,看着对面某个不安分的器官:“管好你的脑子,在这里动了贼心,没人救得了你。”
——虽然理论上是二对二,可是真动起手来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想起那对冷极的眸子,汪沛金战战兢兢地吞了口唾沫,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强行将那些龌龊的念头从脑袋里抽离出去:“记……记住了。”
汪十方见他表态了,欣慰地关闭了自己的手电,枕着背包躺下,幽幽地叹气:“珍惜这八个小时吧,之后可就没这么舒坦了。”
于是汪沛金也有样学样,背对着远处的光源躺好了,两组搭档各自占据一个角落,互不干涉。
汪荧将外套彻底脱掉,只剩下贴身的小背心,用牙齿咬着绷带给自己包扎。
因为她抬手的幅度很受限制,动作因此显得有些迟缓,但是因为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什么表情,看不出一点焦躁,又莫名透出些许宁静出尘的禅意。
汪灿在她面前蹲下,自然地伸手接过绷带:“不是叫我来帮忙的吗?”
汪荧的目光停在他手腕上。
下一秒,汪灿抽手,但汪荧的速度更快,瞬间就抓住了想要抽离的指尖。
汪灿一怔:“你……”
“别动。”她头也不抬,轻轻托住汪灿的手心,使他的腕部保持放松的状态,抬高至心脏以上。然后保持着这个角度不变,手指贴着他的掌心向后移,最后只用无名指垫在掌根处,双手小心翼翼地撑开袖口,将袖子往上卷,露出鲜血淋漓的右手腕。
——刚才那些鱼钩在汪灿腕部留下了数道长短不一的伤口,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条都曾深深地嵌进肉里。
手腕中间那道伤痕是最深也最长的,目测有十几厘米,要是角度再偏一点,就会割断他的肌腱。
汪荧看着那些伤口,脸上流露出一种痛楚的表情,用手电筒一一照过那几条血痕,每检查一处,脸就白上一分,直到全无血色。
但就算这样,她拉住汪灿的那只手也仍然是稳的。
汪荧深吸一口气,隔了很久才呼出来,单手去翻医药箱,竟然一下子碰倒了药瓶,摸索了几下才抓到手里。
由于姿势别扭,汪灿没法去帮她捡药瓶,但是左手下意识地握住了她的右腕,感觉到她只是虚弱地挣扎了一下,甚至没有力气做出第二个表达抗拒的动作。
这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