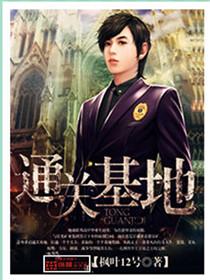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许茹芸突然想爱你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哭什么?”他问。
施想想有些囧,她抽了抽鼻子,眨眨眼,把盈在眼眶里的泪流回去。她说:“你不开心吗?”
景宴的手指一顿,背影一时间有些僵硬。你开心吗?你不开心吗?这样的问题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问他了。开心对他来说是一种珍贵无比的感受。
他用自己的沉默无言来抗拒她的过分亲近。
施想想抿了抿唇,即使努力压抑,还是抵不过喉间的疼痒,忍不住咳了几声。她心虚地看了一眼景宴,生怕他觉得自己吵,然后把她轰出去。
但景宴没有,他只是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拨号码,淡声道:“叫医生。”施想想一惊,立刻起身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拦住,使劲摇头:“不用,太麻烦了。”
她哪有这么金贵?咳两声,吃个药就好了。叫一声也太夸张了吧,她又没晕!
“麻烦?”他挑眉,直视她,反问,“那为什么没好?”说完,大约是看到施想想那霎时间亮起来的眸子,满是暧昧,便又别扭地别开脸,脱开她的手,解释道,“你没好会影响我拍摄。”
施想想忍不住抿唇一笑,不管他怎么说,她就是很开心,哪怕只是一句客套的关心,她也觉得很甜蜜。这些年的喜欢,完全是她一个人的路程,而今天,她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与他对话。
班书送来了药,进来时,他那一双眼,把两个人左右看了不下一百遍,努力想要找出破绽。施想想吃了药,又把口罩戴上。
似乎是察觉到景宴的目光,她解释道:“我感冒还没好,传染给你就不好了。”去年他巡演的时候因为过于劳累,得了重感冒,好几月都不见好,可把她心疼坏了,想到这个,她就得十分地小心。
谁知,下一个瞬间,她便见那人起了身,倾身向前,身处那双手轻轻地划过她的耳廓,她身子一颤,脸上的口罩已经被他取了下来。
她的耳根子起火了,一脸绵延,烧到脸上。
“我不介意。”景宴说着,又十分自然地坐回沙发。他手里握着一支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大约是在写新歌的歌词。这把施想想馋得不行,她坐在沙发的另一边,探头看了大半天,也没瞄到。
见景宴写的认真,想想,景宴把她叫过来,总不是让她干看着吧?于是,她大着胆子走到景宴边上,弯下腰,倾着身子,想要看一看。没想到,景宴却把本子一收,往边上一挪,便遮了个严严实实。
她有些郁闷的撅了撅嘴巴:“我不能看吗?”
“不能。”
“那我来这里干什么?”施想想不解地问。
景宴眼神微动,他的笔顺停了几秒,又继续写,他说:“你可以回去。”话音刚落,施想想连忙警惕起来,她迅速地跌坐在沙发上,摇头:“不,我不走。杀了我我也不走。”
开什么玩笑?难得和景宴见上一面,她可要好好珍惜,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景宴:“……”
他背过身,唇角弯了一下。他是不明白,这个女孩子说话为什么能这么……“厚脸皮”。
施想想见景宴不理她,便自己捣鼓起别的东西来。她从包包里拿了一张纸,坐在沙发的另一侧,也开始写写画画。偶尔,还拿着手机这边摆弄一下,那边摆弄一下,时不时偷笑两声。
班书隔三差五进来一次,有时候是送文件,有时候是送甜品,但每回来,那眼睛都要在两人身上扫描几百遍,想像个侦探一般。
时间缓缓从他们之间流过。施想想写了半天,也哼了半天,人是愈发地困了,她想开口问景宴,可景宴的神情是那么地专注,仿佛天地万物都与他无关。药效上来,满身疲惫的她打了个哈欠,本想挨着就好,却不料一闭眼,就睡过去了。
景宴的眼角余光再次看到施想想时,她已经像一个猫咪一样,微微的蜷缩着身子,静静地沉睡着。外界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有无穷的灵感,随便一写,就能写出一首歌。可是今日,他发觉自己的心有些不平静,他才下笔写了一句,就能看见那个女孩子偷拍他的动作。
敞亮而明媚。
喜欢他的人那么多,可不是每一个,都能走到他面前的,她是第一个。
他眸子有些不悦,抬手揉了下眉心,同时,人也起身,随手把挂在架子上的西服披在她身上。走之前,他瞄到她手心里摊开的那张纸,上面涂涂改改一大堆,黑不溜秋,只依稀可见几个字。他的良心只迟疑了几秒,随即轻轻拿起,只见上面写着的,是他和她的名字,两个名字之间还画了一个爱心。
-
施想想饿醒了,醒来时她发觉自己身上多了件外套,那外套上海存留着她的温度。她摸了摸,心里顿时软得跟棉花糖一般。
他是在关心她吗?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人,正好是班淑。班淑是接了班书的电话过来接施想想的,她把手里的外卖放在桌上,说:“吃饭,吃完吃药。”
“哦……”施想想纳闷着自己怎么睡着了,她环顾四周,也没看到景宴。班淑知晓,便道:“还没看够?他去工作了。”
“啊?那v剧本呢?”她惊诧,不是让她来讨论剧本吗?班淑却比她更震惊,她反问:“怎么?一个下午,你们还没讨论剧本啊?”
“那你们干什么去了?你别告诉我,你在景宴这睡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