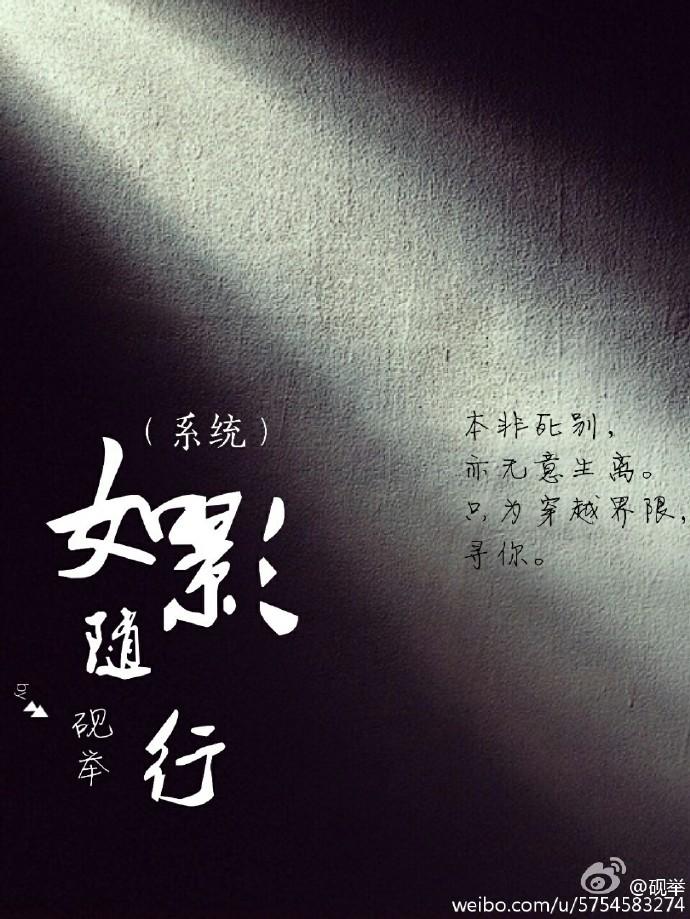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醉春归 > 43 第 43 章(第2页)
43 第 43 章(第2页)
邵代柔噗嗤一声笑出了声:“呸呸呸,瞎说什么。”
“食盒的事,东家说了算。”卫勋竟开起了玩笑,“我不过一届短工,自然全凭东家吩咐。”
“行呗。”邵代柔自然而然拿起了东家的架子,挑着眉毛吩咐下去,“我挑着可以冷吃的花样做几道,摆个食盒,我们带在马车上吃,马车里有炉子也不怕冷。就这么决定了。”
她连说还带比划,连食盒的模样都在卫勋眼前浮现,他看着,听着,过往他对一个家其实并没有太多想象,他的父母固然互敬互爱携手半生,但卫勋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他的父母与其他夫妻大抵是不同的,他们可以放心将后背交给对方,却温情不足。
兴许家的温情就是这样的,她会为他细细量过尺寸裁衣裳,也会早起亲手做一份食盒,悉心拣选着适合外带的菜式,严丝合缝地掩上盒盖,盖住那一匣细腻的柔情。
忖度及此处,就连卫勋自己也觉得矛盾,好像一时又欣赏独立能干的女人,一时又流连女人的体贴和温柔。
其实想穿了也没那么复杂,所有这些临时订立的标准,似乎都是比照着邵代柔来的。他只是见到了她,她是什么样的,他就觉得什么样的很好。如此而已。
很容易就理清楚了结论,但他没打算顺着这番结论再往前延伸出什么,到此打住是最合适的结局,难得糊涂。
他面前的邵代柔冥思苦想半天,很严肃地提出:“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什么?”
卫勋挑眉看她。
白日的亮光逐渐落幕好像也不要紧了,她那极为认真的眸光已像月华初上。
“我得去雇一辆马车。”她严谨地计划着。
明日搭乘马车出行,邵代柔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卫勋是什么身份,总不能让他跟她一样在大街上用脚走路吧。
骑马?她又不会骑,她只骑过驴,骑马跟骑驴是不是差不多的?
她这人,要做什么事都得一往无前,但凡琢磨到后来,必然都会变成瞎琢磨。
正瞎琢磨着呢,只听卫勋轻笑一声:“罢了,这些都交给我,大嫂只管带上自己。”
他还哦了声,“最要紧的东西别忘了,还有你的食盒。”
邵代柔有心让他别冲她再笑下去,再这样,她怕是真要以为自己天生就与他如此要好了。
“噢……晓得了。”她低声喃喃。
怪事,他也没说什么吧,怎么赧得她脑袋都垂垂低下去。
旁边的客栈迎来了一天之中最为忙碌的时辰,人们忙忙碌碌一天,盼的就是傍晚过饭时泥炉上刚端出来的热热烘烘一碗浊酒,仰头灌下肚子,迷迷瞪瞪的,才觉得这人生过得没憋屈到尘埃里。
只不过吃多了酒嘛,难免就脸红脖子粗的,将人生中那点不起眼的经历当作谈资,开始夸夸其谈,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也有,再被旁的人好生劝开。
一堵矮矮的墙隔开了两个世界,墙那边人声鼎沸,这一头呢,不过一墙之隔,偏又是这样的静。
邵代柔努力在逐渐稀薄的光线里盯着他看,突然发现了什么,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比划,比照着他的玄狐毛领。
“怎么?”
“你——”
骤然一阵大风扑过来,一并将她细细的声音卷走,她徒劳地低喊着:“领子!我说!你衣领上沾了东西!”
极佳的耳力也罢,能够观口型辨声也罢,依然有什么在身后丝丝缕缕地牵扯着卫勋,让他什么也没做,静静看着她一点一点伸手探过来,把肩头那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