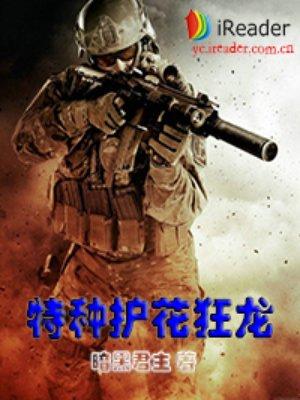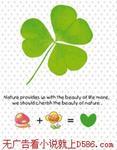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猎物者和新猎物者的区别 > 第49页(第1页)
第49页(第1页)
把我安抚下来之后,辟尘仍然不死心,要继续做它的猪手,即使我一再声明那碗蛋炒饭已经足够使我感激涕零,下辈子都对它情深一往,辟尘照样不管不顾,摸出了桂皮八角,酱油冰糖,大批炉火器具,以精细程度而论,即使是纽约知味轩也未必有我眼前那么专业的厨房。如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坐着不动,只好长吁短叹再次出门,去找一瓶“一闻就会让我晕倒”的正宗绍兴黄酒。一个人走到街上,感觉回到了多年前的猎人时代,入夜,带一瓶啤酒去地铁站等着蚯蚓出来给我表演“时尚八卦深夜开讲”,懒洋洋晃回家,被辟尘的一个枕头打得满地找牙。那是好日子吗,或者只是我不曾有任何担忧的日子?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漫无目的走着,等待一瓶绍兴黄酒的气味从瓶口破空而来,将我打昏在地,不过,真正差一点把我打昏的,却是一条断腰鱼。这条平常生活在马那亚海沟,不过偶尔会到陆地上四处看看,买买衣服什么的断腰鱼从天而降,笔直落在我的脖子上。当我把它抓下来的时候,它的头和屁股贴在一起,还在气急败坏嚷嚷:“不许插队,不许插队!”我很耐心的等它吆喝完,然后弯腰问它:“你从哪里来的?”它跳到地上,怒气冲冲的把自己打开―――跟打开一把折尺一样,白了我一眼,然后说:“你?乡下来的?赶紧回乡下去吧,我没功夫理你!”说不理就不理,它的大尾巴在地上一点,整个身体弹跃而起,向前飞去,动作虽然有点傻,不过速度却奇快。我摸摸脖子,想不通啊,它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行,我要追上去看看。尾随着这只跳来跳去的断腰鱼,我一路狂奔过了两条街,来到了一个y字形状的路口,四际无人,漆黑一片,唯一亮灯的地方仿佛是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面,而就在这店面门口,大批各色非人正排成一条长队,吵吵嚷嚷,热闹非凡。很显然它们的社会公德修养还不到位,冲突时有发生,不断有三两非人从队伍中飞出来,呼的一声,不知道被甩到哪里去了。嗯,我现在知道断腰鱼是怎么跑出来的了。作为一个喊出过:“不好奇,毋宁死”口号的前猎人,此时我要是转身就走的话,下辈子都一定会睡不着。所以我忠实秉承了自己的本性,满脸激动的挤到了队伍的最前排,扒在一只食金兽的背上,刚想定睛看看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清仓大甩卖,居然可以吸引如此多的另类观众,身后一阵骚动,好似又打起来了,一股大力在我背上一推,我一个跟头,栽了出去,栽进了一扇门里。眼前是一片温柔的烛光,摇摇照耀着这间小小的屋子,除了错落分布的烛台外,空无一物,在我的面前,一块巨大的黑色帘子垂下,有个声音幽幽的问我:“你要什么?通行证还是算命?”这声音好生耳熟啊,好似故意压低了,一下子又听不大出来。出于某种本能,我也憋了一口气,哑着嗓子说:“算命什么价钱?”答:“批流年可以贵到你出鼻血,也可以由我倒贴你一点去买张草席包包,看你命如何啦,先把生辰八字报来,测字也可以,你随便说一个字。”这番纯粹业务性的介绍完毕之后,那声音非常低微的嘟囔了一句:“妈的,饿死了,今天生意怎么那么好!”我的妈呀,难怪我说听起来耳熟,这是狄南美啊。三年前,她突然从墨尔本消失,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此后偶尔有一个电话来请教辟尘如何处理毛衣起球问题,或者我在家里天台上唱唱山歌的时候会听到她中气十足的千里传音,通常是:“小破,我的乖乖,猪哥,你唱得难听死了。”诸如此类大逆不道的话。最后一次联系,就是几个月前教了我一个狗屁建筑防护诀,害得我几乎终生贫血。对于我们来说,她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担心,我们担心的反而是那些生活在她周围的人,一天到晚笼罩在这只脑子随时进水的狐狸阴影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倒一次哭笑不得的大霉。老狐狸看起来混得不错,开店当个体户了,我敢担保,这家伙一定偷税漏税的。听我半天没反应,她开始催我了,说:“到底要什么,你赶紧说呀,我收工了要去吃夜宵的。”奇怪了,以老狐狸之通灵,居然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是我?饿坏了吗?不管怎么样,先算一算再说。生辰八字?还是测字?给她看手相是一定不行的。她要发现是我,随便一激动,三昧火出,我的爪子就熟了。说到我的生辰八字,老狐狸还真不知道,她说一旦知道了,一定会忍不住要给我算命,而且算得无比仔细,但凡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自然无法坐视不理,只能出手去修正我一生所有可能存在的错误,最后泄漏天机,妄改人命,多半连累我和她一起被雷打死。既然她说得这么严重,我也不好意思太过勉强,所以除了偶尔发愁出门应该穿哪件衣服,或者头发要剪成什么样子我会去问一下南美的专业意见以外,其它事情我都自力更生,最多丢坏一两个铜币,总会有个结论出来的。还是测字吧,昨天那么多倒霉的事,我希望有一个好兆头,所以说了一个吉字。测最近行事的运气。南美心不在焉的嗯嗯两句,我几乎都可以听到她肚子发出的咕咕声了,天哪,为了做生意她居然饭都不吃啊,难道是勤劳致富这句成语感动了你?我正在偷笑,南美忽然在帘子里抽了一口冷气:“士之口言事不祥,行途拮据,无手则孤,有手而困,是之两难。糟糕,真糟糕,小子,你最近要去做什么?”我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那帘子刷的一声拉开,南美盘腿窝在后面的一个大豆袋椅上,圆溜溜的眼睛不可思议的瞪住我:“猪哥?你怎么死到这里来了?”我和南美这么难得的一出相见欢,结果在一片骚乱中结束,这骚乱固然有我们的一部分贡献,不过主要还是由屋子外面那些混蛋非人造成。当时南美正把我骑在地上打,骂骂咧咧的教训我居然到了东京也不说一声,还乔装打扮跑来消遣她,实在其心可诛!也不管她自己这只流浪狐狸居无定所,一向神出鬼没,我的追踪术再怎么精通,也决计不可能发现她在此地开店啊,否则早就来入股了。她打得上瘾,还要去找根蜡烛来滴我的时候,忽然轰隆一声,这间房子临街的那面墙,倒了。整面墙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那么大声的,绝望的,委委屈屈的,倒在了地上。我和门外还在排队的兄弟们不约而同张大嘴巴向天上看,在这面墙和天花板接壤的地方,有一个俊美的男子悠闲的坐在那里,他的手还插在水泥钢筋的墙壁中,如在切割一块柔滑的芝士蛋糕。白色的过膝长衣,一双毫无感情的蓝色眼睛,眼波流转过下面的熙熙攘攘,仿佛牧场的猎人在清点他的牛羊,当看到我这只羊的时候,他似乎有点惊讶,手一撑,轻巧的跃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外面的非人们发出了杀猪般凄厉的喊叫:“破魂啊,破魂啊。”转头如潮水般散去,飞的飞,跳的跳,可是走不多远,却又拥了回来,在他们的身后,东南西北四个角上,精蓝修长的身影在夜色中也刺痛着我们的眼睛,逐渐向大家逼近。我满头大汗,心里的小鼓打啊打啊,南美在我身边问:“怎么样,打还是跑?”打不过,跑不赢。逃命的法术有没有?我反过来问她。南美白我一眼:“我一辈子不逃命的。”我哼一声:“那你还问我打还还是跑?”她摆开架势要跟我来一场辩论赛:“逃命和跑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打不过,后者是不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