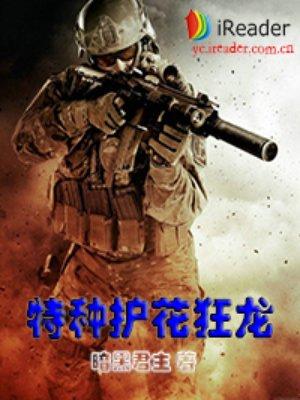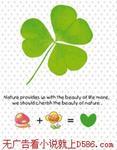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猎物者和新猎物者的区别 > 第39页(第1页)
第39页(第1页)
万事都已具备,只要顽抗到底。这时候辟尘做完了早上的例行清洁,跑来做劝降工作,深明大义,语重心长的说:“猪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你认命啦,反抗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两年我们也没存什么钱,到时候受伤了,医药费又高,一下子又搭进去了。哎,这工作不好找,下半辈子怎么过啊~~~”。光听他说,完全可以认为该八卦犀牛已经被江左司徒买通,多年来一直潜伏在我身边当卧底,说不定连我时常偷吃小破的营养饼干以及提前教育他看美女要去地铁站出风口附近这种不上台盘的事情都时时报告,大大影响我下辈子的令名。可是我岂是那么好欺负的,当即明察秋毫的指出,不知道是谁,一边在这里唧唧喳喳,一边不停手的给碉堡包重尘,包了一层不够,已经开始包第二层了。包得如此彻底,逼得我直着脖子喊:“笨蛋犀牛,留个地方给我透透气啊,喂,全堵了~~。”这么耗着,上午三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我把带进来的饼干吃完一半,终于觉得有点不对。奇哉怪也,江左司徒迟到了哦。莫非光行知道我舍不得小破,直接把他丢到喜马拉雅山顶上反省去了?唔,不太说得通。光行小朋友虽然挺讲义气,不过生平的口头禅乃是“安全第一”,要他冒险犯禁,除非拿伽马刀架到他脖子上。胡思乱想揣摩了半天,辟尘又跑进里面去了,少了他的罗嗦,我突然觉得周围异常之安静,一点奇怪的微寒感觉自脚底缓缓流窜而上,行经四肢百骸,却不知道来自何方。我情不自禁的问:“小破,你冷不冷?”他没有答我。很久以前,我已经开始着手训练小破防火防盗防江左司徒的警惕意识。终于使他无论身处何方,正在玩的是毛毛虫变种秀还是十米深的地下泥巴城堡,只要我打个呼哨,他过来跟我爬进碉堡挤在一边,激动情绪溢于言表,不停的问:“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我说“没来呢。”他立刻大点其头:“哦,那不要说话,安静,嘘。”然后身体扭得跟团麻花一样,四处打望,望上两个小时都还是没有,其心情仍然无比兴奋,破魂的耐心可真不错啊。现在大异平常,他居然没有答我。想一想,除了进来的时候,他还乐呵呵的嘀咕了两声来了没有以外,似乎就此打起了瞌睡。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要对他睡或不睡下定论的话,单纯根据目击信息进行分析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本来小破的眼睛长得就和辟尘一脉相承,且朝夕相处,青出于蓝,到后来,他有没有这个器官就已经让初次见面的人很费思量,至于说要一眼就确认此人是不是处于清醒状态,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列入明年亚洲猎人联盟五星级考试的项目之一。那种寒冷的感觉越来越怪诞而深入,令我十分不舒服,趋前我摇摇小破,轻轻喊:“宝宝,宝宝?”他可爱的小脸安静的偏向一边,一动都不动。小破三岁过后,身体停止成长,模样也没有再变化过,我们终于能够放心让他出去参加什么同学生日会之类的交际活动,而不至于担心一顿饭之后主人家跑出两个一摸一样的儿子,而我们家的不见了。他的饮食习惯更加多元化之余,日常起居规律也跟一切同龄小儿均无两样。有时候,我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身世来源,辟尘这个笨家伙,还屡次花费功夫穷想我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怎么有个小孩结合了我们两个的面部特征?光这么猜一猜,就已经搞得我好久没心情吃饭。如果说,这一切都还算是好消息的话,让人悲痛的就是,小破的常规智力也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所以他的幼儿园上了一年又一年,从最贵族的到最贫民区的,从最管理严格的到最松散敷衍的,从最先锋理念的到最违背人性的,无论去到哪里,每年的年终考试成绩都差不多。除了体育永远a后面十七八个加号以外,其他都逼得老师迫不得已的出到了x,要不是我苦苦哀求,或者直接给z也未可知。只有一次人家给了他全部科目及格,却完全跟他的学习成绩没有关系。该幼儿园所坐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少数民族犯罪社区。四周环境如何且不说,读幼儿园的小孩子都成立诸多帮会,动辄绑架同学,或向不顺眼的老师发出死亡通缉令。刀光剑影不算什么,后来直接出现了特制的微型沙漠之鹰。那里所有员工的统一装备是国家级特种部队用的那种防弹衣,背心统一绣上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自从小破去了之后,突然之间,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反正问题幼儿们都清一色变成了乖宝宝,其柔顺听话的程度,屡屡把校长感动得流下泪来。于是整个幼儿园变成一片真正的人间乐土,带动附近的凶杀抢劫率随之大幅度下降,史上第一次,一家幼儿园的校长拿到了墨尔本市的社区安全贡献奖,然后他敲锣打鼓的送到了我们家。同时送上的,还有完全昧良心给出的全科目及格年终报告。我和辟尘辗转八方,苦心孤诣,为了他的教育问题操透了心。尝试过了填鸭,引导,催眠,拷打,(实施过程中还因为动用暴力自食其果,我躺进猎人医院住了好久)等多项教育手法之后,我们终于无奈的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破魂在以武犯禁一途上确实高山仰止,令我辈景行行止,望尘莫及,但是提到如何学习两位数的加减法,他彻头彻尾就应该划入智障儿童那一群。不过,就算这样,我还是爱他的。笨小孩也有春天啊。伸手把小破抱过来放在臂弯里,轻轻摇了摇,看着他甜美的小脸,一种条件反射的忧伤情绪传来,开始在心里大骂江左司徒:什么整人的方法不好用,非要当初派这样一个劳什子任务给我,先占用了我生命里最宝贵的七年时光把我送上天伦之乐的珠穆朗玛峰,然后二话不说,一脚踢在屁股上,不出两秒就掉到了大西洋里,往四周一看,和我做伴的居然还是一群饿了好几个月的鲨鱼。够狠吧,喂,救生圈给一个好不好?骂着骂着,我的手臂为什么感觉到沉甸甸的?是小破?小破不过十七公斤而已,我眼下抱的却好像一块玄铁。不但沉重到将我整个人都往地上带,而且初初那一点冰冷的感觉,已经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寒,最令我方寸大乱的是,这无穷无尽越来越猛烈的寒,竟然是来自小破。转眼之间,他的小小身体骤然降温,传来的是冰凉刺骨的触感。我惊慌的把他颠了颠,叫到“小破,小破,你怎么了?”没有回答,没有表情,没有任何有知觉的表示。他仿佛在顷刻之间,整个人沉浸到了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所在,那里没有光也没有热,只有无止境的冰冷的蓝。之所以我没有说是无止境的红,是因为同时在他的皮肤外层,隐隐出现了蓝色水晶般的碎粒,仿佛一双无形的手在他周围飞快的编制一件密不透风的毛衣一般,水晶粒凝结成薄壁,飞速向四面蔓延在空间里,由脚部开始,把他完全包裹住。仿佛是重演我多年前在破魂牧场看到司印熔化的那一幕,该来的始终都要来了。我仍然紧紧的抱着他,心中的感觉无法以言语形容,每一秒可以看到他面容的时间都那么可贵,因为这一秒过后,也许终此一生,他都只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而记忆那么模糊而无助,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卑微的安慰。想到这里,我跳起来大喊辟尘:“辟尘,辟尘,赶紧来啊,小破冬眠了,小破~~。”话音还在碉堡里嗡嗡的回想,辟尘已经哐当一声摔落在我身前,光线也马上好了很多,看来他解开重尘罩的功夫比织起来好得多。爬起身看到小破的模样之后,辟尘的嘴巴立刻顺应地心引力张得史无前例的大,生平第一次犯起了结巴:“怎~~~怎~~么啦?小破~~~小破~~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