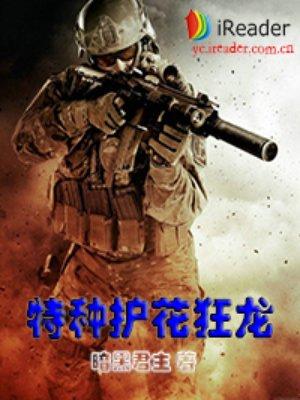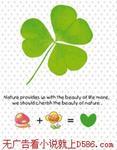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猎物者和新猎物者的区别 > 第19页(第1页)
第19页(第1页)
才七点,七点而已,大家居然都跑去睡觉。我提议开一个野营晚会,大家唱唱,做做游戏什么的,其他东西都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疯子。屈服于这种强大的暴民意志之下,我成年以后,入土以前,第一次,我发誓也是最后一次,七点十五分,忍气吞声的钻进了一个帐篷准备睡觉,而且还是跟辟尘同床共枕。猪哥,你在纽约那边看到了些什么?它一边把睡袋打开,一边问我。我叹气,满脑子顿时又是那些该死的尸体,栽在垫子上我告诉它:“我看到了好多吸血鬼被人家当猪仔赶,然后又看到好多尸体在天上吊起,头痛啊。”它却见怪不怪:“怪事天天有呀,不要这么孤陋寡闻。”我凑近它强调:“好多尸体在天上哦!”它当的一声倒头就睡:“你要是还想看,我立刻可以让整个广州都跑到天上去。”我立刻噤若寒蝉,我可没有忘记,辟尘虽然在我面前天天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养只拖把当宠物,不过它是净空领域数一数二的高手,净得过了头,会出现整体真空的恐怖效果,还是不要惹它的好。至于尸体,大概全世界都死完了它也只管我在不在吧。时间还早,不过这里是白云山未开发的最高峰,人迹很少了。奔波了一天,我也挺累的,将就一下睡吧。身边的辟尘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开始打呼。刚合上眼有点朦朦胧胧,脚上有东西碰碰我,一惊醒来,我呼的翻身坐起。张晚仪吓了一跳,向我招手:“嘘,别出声,出来。”我一身冷汗:“干什么,好晚了,我要睡了。”她却伸出手来拉住我往外拽:“来啊,来啊。”我连滚带拖出了帐篷,她放开我,背过身去看天:“看,多漂亮的天空。”要我看天空?乘我抬头,一刀插进我的喉咙,这里到处都是树,也不用运回中信了,直接埋掉。哼,我才不上当。于是我夹着喉咙身子往后仰,一边配合她啧啧称奇:“啊,好漂亮,好漂亮。”心里暗骂:“漂亮个鸟,我什么天空没见过!”她对着我笑:“猪哥啊,你们这些人都好有趣哦,这几天啊,是我一生最开心的时光了。”她咬着嘴唇,穿了一条长而宽敞的蓝色裙子,在山风中飘飘欲仙。沉默半天,我还是夹着脖子,不过换成了看她。她又笑。然后说:“我是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幸好脑子不错,去读了书,有份工作,不过这么多年,真是很孤单。”我默然。这句话我感同身受。没有家的人是很孤单的。冒死保辟尘,就是因为它在哪里,我就感觉哪里有我的家。咿,原来半犀还有这种使人宾至如归的功能哦。一句话到了嘴边,我把它吞了下去,我想问:“是不是你太需要人家的爱,所以得不到的时候,就把他们杀掉了事。”夜风如手。深蓝色天空中群星闪耀。山峰静谧而悠远,在空中剪出美丽轮廓。懒洋洋的望望四周,晚仪在朦胧中的微笑令我心里平和喜悦。真奇怪,我生平在无数地方见过无数山水,从未有过这一刻的感觉。有句话说,重要的不是做什么,在哪里在,而是跟谁做!所言非虚!我本来认定她是杀人凶手,此刻却大逆不道的觉得没什么关系。也许她并非人类,猎人来抓她,防卫过当杀人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明显是我色迷心窍状态中的推论,作不得准的。无论如何,还是跟她相处下去吧,时间会给我答案,也许有一天半夜江左司徒就来托梦给我说:“兄弟,welldone,你可以把她交给我们了。”至于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交而现在不可以,我必定一样莫宰羊。张晚仪突然问我:“你爱南美吗?”我肚子里抽起筋来,闷着头想想,说:“我不爱她,她是个狐狸精。”她轻轻打我一下:“别胡说。她是你未婚妻。”我心想谁要是有这样一个未婚妻,直接折寿一百年,认识当天晚上就应该往生极乐,免得麻烦。但是这种在一个女人面前编排另一个――真的也好假的也好―――的缺德事,我还硬是做不出来。因此当晚仪接着问:“你不爱她,为什么要订婚呢。”我只好继续闷头做忧伤状,答:“因为我要对她负责任。”我相信这种对话在人类世界的痴男怨女中一天要发生几千次,通常男方都会比较王八蛋一点。不过今天我这个王八蛋当得有点冤:我对狄南美负责任?谁对我负责任啊?怅然的看着她不再说话,慢慢走回帐篷去,身影娇柔,我见犹怜。突然间,意外情况发生了,她停下脚步,惊讶的望向紫罗和暴的帐篷。帐篷里传来紫罗低沉的呻吟,声音甜腻而缠绵,身为成年人,不可不知什么剧目正在上演。晚仪掩住嘴轻笑,向我招手示意走近去偷听。哼,这么丢人的事情我才不做,我站在这里已经什么都可以听到了。这瞬间我不期然想起离开广州那天晚上,晚仪美艳绝伦的身体就在我眼前,居然没有吃,真是罪过。看样子她也想到了同样的事情,夜色里我也看得到她脸上的绯红,悄悄的看我一眼,又赶紧回过头去。据说女人是最恨那种情况的,因为通常表示自己没有魅力,或者看走了眼,吊到的凯子是天阉~~~我想会不会保罗兄弟诸人,就是因为太执着于争当柳下惠才把她杀心惹翻的。嗯,下次她再请我去她家里,我一定要提前去买一条颜色花俏的内裤,表示我对她的无限热情~~她一翻帐篷门闪进去了,我才能收回自己的眼光。紫罗还在呻吟,考虑到它们当夫妻当了好几百年,还有这样的兴致,实在值得上知音杂志加以表彰推广―――顺便说一句,这本中国杂志我很喜欢看,实在八卦得登峰造极!他们那么投入我就更加孤零,还是去睡觉好了。走了两步,猛然间醒悟,不对啊,他们两口子是蜘蛛哦,所有动物里面只有人类和海豚比较有情趣,会为了取乐做爱,其他的都背负了重要的传宗接代任务。就算它们修炼得法胳膊粗了,怎么也扭不过造物主这根大腿去啊。我径直过去踢一脚它们帐篷门,问:“怎么了?”“哗啦”!一道闪亮的锋芒蓦地突破帐篷,划过我眼前,我本能的往后一跳,定睛再看,暴大汗淋漓地伸出头来,无言死死盯着我,帐篷里,紫罗现出了原形,卷曲在地上,八只脚无力地摊开两边,不时一阵痉挛。她的腹部微胀,透明发光,隐约可以看到其中有无数黑色微小的圆颗动来动去。我一见大惊,抢进去一搭她的心脏,跳得极慢,“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暴浑身颤抖,惊惶得手足无措,只会看着紫罗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把推开他:“去叫老狐狸来。”不用他叫,南美已经冲了进来,我冲她喊:“索姆虫破卵!按住紫罗,她很快要发狂了。”从随身携带的修复箱里取出我锋利的解剖刀,照紫罗腹部迅速横竖各划一道,腹壁如妖花怒放般绽开,破出一个极大的口子。在口子里,无数纠结在一起,无头无眼的黑色圆形蠕虫,有着濡湿外表和密密麻麻长满全身的鲜绿色疙瘩,正在紫罗肚子里翻滚腾跃,有一些在主血管附近,似乎逐渐要挤压进入血管。新鲜的空气涌进腹腔,虫子的活动在瞬间停顿下来,然而也就是瞬间过后,突然间更紧密的纠缠成团,形成一个巨大的球状体,我用刀尖试图去挑动它们,未曾真正接触,那球状体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随着尖叫声中心破开,如同一张森森利口,猛然向我吞噬过来。索姆虫是天生寄居在紫罗和暴这种八味草蛛身上的微型恶性生物。每逢十三年发作一次,严重的时候会将寄主整个身体生生吃嚼干净,如果不做措施救治,寄主在被吃成一个木乃伊之前,由于剧痛和神经损害,一定会狂性大发,六亲不认。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不过它也恰好有天生的克星,在八味草蛛栖息的地方,通常都会生长一种湿头花果,十三年一熟,它们总是定时服用一次,以避开虫噬之灾。我相信紫罗和暴大概是逃避猎人联盟对它们心脏的索求而离开旧地,没有办法及时找到湿头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