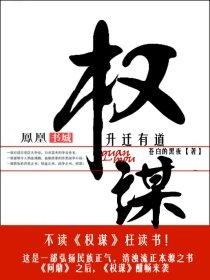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猎物者和新猎物者的区别 > 第6页(第1页)
第6页(第1页)
他也跟着我看:“怎么了?”我大叫:“资料包呢,设备包呢?就这两句话要找到一个人?你当我是全球定位卫星吗?”江左司徒耸耸肩,表情很无辜:“就这样了。”我摇头摇得象得了失心疯一样:“我不去。”可惜敌不过他气定神闲:“不去罢了,你我都知道,勉强别人做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好。不过,你的那只小犀牛现在正在纽约市中心抓狂,半个小时之内,不是美洲猎人把它抓住,就是它发动真空攻击把整个纽约变成无人地带。戏怎么演,全看你了。”看我的结果就是,今天早上十点钟,我坐在中国大陆南方的一个澳热房间里,长嘘短叹,一边从各个口袋里往外掏零钱,交给辟尘去买菜。晚上,吃过了辟尘做的醋溜小白菜和广东香肠,我们坐在一起商议谋生大计,窗外华灯万丈,亮如白昼。辟尘巡视了一圈食物储存量,把剩下的零钱数了七八次以后,郑重发出哀的美吨书,曰:“你要是不马上去赚钱的话,我们还可以顶五天,五天后处于纯饥饿状态,以你我的体魄,还可以挺十五天,然后我把你吃掉,又可以顶五天,五天后再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有天知道了。”这后娘嘴脸着实可恶,不过我也必须承认它所言不虚。其实真正可恶的是江左司徒,既然请我来找人,除了住所之外,怎么也应该预付一点定金吧,否则猎人还没有开始捕猎,先饿得半死,成何体统。当然,请之一字,用在我和江左司徒身上实属牵强,不过任何力量都不会比贫穷和饥饿更可怕,所以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江左司徒叫我干的事情干完之前,我一定已经成为相当资深的舞男了。辟尘听到这句话眼睛一亮,居然马上伸手过来数我的腹肌,且发出感慨:“猪哥,不如你明天早上起来跑步吧,我看你肚子有点松了。”我一口气没有转过来,几乎当场倒地。它还不肯罢休,在一边列举我可以干的营生,统统上不了台面,包括:卖血。理由是我经常受伤流血,有时候一次可以损失一千毫升,既然这样都不会死,那不如直接拿去换钱。保安。人类里面能跟我打架打赢的应该比较少。人体炸弹。我可以自愿到巴基斯坦去和当地游击队商量,成为专业人体炸弹,因为一般当量的炸弹都炸我不死,所以我的优势在于可以重复利用,环保节约,他们一定喜欢。模特。我身高一米七八,稍微矮了点,不过它说我比例不错,虽然上不了巴黎时装发布台,在广州哪个草台班子混混应该是凑合的。二奶。听到最后两个字我实在忍无可忍,跳起来就跟它大打出手,并且呼口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它绕着屋子一边跑一边劝我:“猪哥,面对现实吧,你愿意干,人家还不见得要你呢。”正打得热闹,一阵突如其来的砸门声传来,我和辟尘面面相觑,凝神静听,确实是从我们大门口传来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人在大力踢门,发出当当当的撞击声。想想我才来广州一天,谁会来找?莫非精蓝被我暗算过一次怀恨在心,现在趁江左司徒不在,跑来打我?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我开了条小门缝,看了一眼就赶紧叫辟尘:“快,把吃的全藏起来,是狄南美。”结果人家抢白我:“狄什么美,神经病!”这个人家就站在我门外,足有一米七高,金色热裤,黑色背心,两条长腿哇哇哇,足以令所有非基老的雄性动物流下口水,假睫毛,尖尖脸,唇红齿白,扑的粉太厚了,不停的往地上掉,活生生就是狄南美在交游网站上放的那张照片的真人版。难怪我第一眼还看错了。她不是南美,她是一个真的人。我的死狗德行即刻出笼,点头哈腰:“您好,有什么事情吗?”她恶狠狠的瞪着我:“警告你,不要三更半夜唱卡拉ok,小心我砸烂你的门。”撂下这句狠话小姑娘扬长而去,剩下我在这里发呆。三更半夜?卡拉ok?我?你妈贵姓?辟尘面无表情的拿块墩布过来拖地,发表评论道:“疯子。”有辟尘在,无论哪里的人居质量都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改观。当它终于完成了整个房间,包括我的头和脚的大扫除,跑去睡觉之后,天河北的路上,车辆也渐渐稀少了。按道理来说,象我这样一年有大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流浪的人,实在不应该有择床的恶习。今天晚上却很奇怪,床铺和枕头都很舒服,我仍然始终无法入睡――当然我是有点饿了,香肠不大顶用,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饿的时候我会睡得更快呀~~。江左司徒的面容清晰的印在我的脑子里,那张疲惫的脸。真奇怪,身为人类,他拥有的力量却几乎深不可测,精蓝对我脸上挥出的那一拳,放眼整个地球猎人联盟,接得下来的人都屈指可数。但是对他来说,却只需要随随便便一挡。这样惊人的能力,真让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他是做不到的。更想不出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帮手,虽然不用想,这里现成有件事:帮他找一个女人回去。难道我蜗居两年在家后,江湖上对我的风评改了?从独行好猎手换成了电车之狼?虽说停职后穷得要死,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伟大操守,从来没有涉足过色情业啊。换个角度想,这个女人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不可以出动精蓝使用“粽子包裹绑架法”,拿自行车拉回去,搞定收工?江左还要罗罗嗦嗦的交代:“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把她带回我这里来。”我考四星猎人升级考的时候,最后一道实战题是这样的:在死海中找到最有用的一样东西带回来。然后宣布解散,开始计时。当时一起考的山狗听完题目后发了半个小时的呆,弃权,掉头走了。他说这种混蛋程度高到不可思议的题,一定是理事长半夜尿不出来迁怒于人的直接后果。会考的人脑子里一定进了水。虽然他最后那句话影射嫌疑极大―――考到最后一道题的只有我和他而已。我还是厚着脸皮装作没有听见,出发去了死海。在那个鬼地方磨蹭了七八个小时后,随便抓了一个正在淹不死人的海水里载沉载浮,乐不可支的游客回了总部,考官问我何解,我说死海中最有用的东西是人。因为是人在开发它也破坏它,享受它也摧毁它,爱它也恨它,没有人,死海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就不能凸现出来,更不能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杰出案例盛行于世。这段相当于意识流小说中人物独白的答辩居然过关,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我也是从那个游客拿的一本狗屁旅游杂志里临时瞄一眼瞄来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加起来到底想说点啥。我一头雾水。当时我想的是,既然我一头雾水,想来考官们保持头发干爽的机会也不大,不如铤而走险,看能不能蒙混过关。现在江左给我的题目,和之前那个堪称双璧,都是莫须有,无厘头,二百五。区别在于对理事长我可以混,在江左面前就混不成了。愁肠百结啊,我长叹一口气,转个身把自己埋进被子里,顺便打消了起床去吃两块饼干的念头。图一时之快,举手之劳耳,明天早上被辟尘打出一头包,情形未免就有点凄惨:昂藏七尺男儿,因为偷家里两块饼干而被毒打~~~。老天这是给我了什么人生啊。当当当,当当当。踢门声。我本能的去看表,凌晨三点四十七分。难道这两天我受惊过度,开始有点幻听?当当当,当当当。真的是踢门声。我打开门。人版狄南美在外面对我怒目而视:“你,混蛋,声音那么大,你要吵死我!”脸红红的,呼吸很急促,眼神迷离,带着浓重的酒精味道。手里还提了一瓶芝华士威士忌,说完这几句话,一头载了下来,当啷一声砸到我的门上。